 字号:
字号:小
中
大
本书初版于2004年,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美国法律文库”之一,后又被纳入“当代法学名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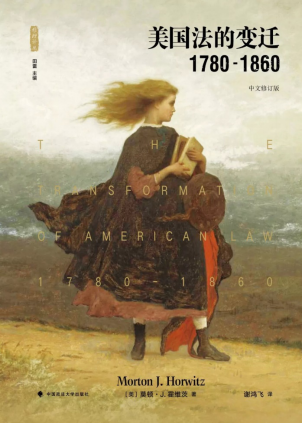
《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
[美]莫顿·J.霍维茨 著 谢鸿飞 译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雅理译丛)(精装)
15年来,本书在国内受到较多关注。除名家代表作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本书描述的这段细微又不失恢弘的法制变迁史中的诸多问题,对正处于国家和社会双重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多少似曾相识,或者正在经历。
将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发展的各种改革纳入“法治轨道”,庶几已经成为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常识,至少是一种法治理想。霍维茨也告诉我们,在美国1780年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是由法律“保驾护航”的,而不是通过税收等公法机制或产业扶持等政策来实现的。而且,本书讨论的“美国法”限于私法的主要原因,是彼时美国推动经济发展,需要破旧立新的法律几乎都是私法。在法律诸领域中,私法历来被认为最具有自然法属性和超越时空的普适性。晚近以来,汉语学界更津津乐道私法超越时代的“体制中立”、“水过石头在”的优势。然而,霍维茨指出,美国低成本发展经济的代价,是由社会中相对无力的、穷困的阶层承担的,私法事实上承载了政治功能,政治不过被转化为謷牙诘屈的法律术语或深不可测法律技术而已;私法的“中立”也最多是一种政治修辞甚至依附于权力的、赤裸裸的借口而已。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州法院在解释征收无需补偿的理由时认为,国家在授予土地所有权时,多给了土地权利人6%,目的是为了保留其后征收土地的权利。工商阶层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推动法院修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规则,在仰取俯拾、稇载而归后,又极力将现有规则固化,不再容许通过变法来侵蚀其既得利益。美国法这一宏观变迁或可概括为“普通法的形式主义——美国法的实质主义——美国法的形式主义”。
不难想象,刚接触本书时这样的观点对我的冲击——简直可用“震撼”来形容。2002年,蒙张志铭教授推荐,我接手本书翻译。当时博士毕业刚工作,在德国历史法学、潘德克顿法学花了不少时间,对部门法制史的研究方法相对熟悉。
然而,如果霍维茨的全部分析仅仅到此为止,可能也像大多数批判法学的作品一样,在让读者激动万分后,除了结论外并没有多少印象。或许还难免受“先入为主”之讥,即先形成观点(甚至是某种感觉和印象),再按需寻求材料。此外,所谓“左派”法学对真实社会中权力结构和运行的分析,中国人早就烂熟于心甚至还感同身受。最后,私法以两个理性人的法律关系为模本,本身就蕴含了权利冲突或权利相互性(霍维茨提到了科斯“权利相互性”的洞见,但未充分展开)。如源于罗马法的所有权绝对观念,在传统英国普通法中也被具体化了(尤其是经过布莱克斯通的努力),它意味着两个相邻的土地所有权人都对其土地享有绝对权,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发。既如此,认为鼓励开发就是支持了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和压迫,可能并不恰当。它体现的毋宁是扶助创新而不是守成,强调财产动态利用而不是静态归属的观念而已,并未涉及双方的强弱。在合同关系中,甲方和乙方的权利也此消彼长,在当事人存在角色互换的可能性时,恐怕也不好得出合同中强者和弱者的对立;本书分析的美国早期保险业发展过程中投保人和保险人角色互换,就是一个显例。而且,这一时期美国法律规则的反复,也说明这一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权力宰制关系说明。也就是说,私法规则践行的结果可能出现经济上的强者和弱者,但私法规则并非预先做了有利于强者的制度安排。
在我看来,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它试图通过对法律进行历史社会学分析,展示今天的普通法规则(这一时期奠定的普通法规则几乎都是今天的主流规则)是如何集中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哪些影响它们变革的重要因素?本书讨论的是农业时代形成的英国普通法规则在美国的变革,它们诞生于权利冲突较少的时期,往往限制了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更不适合经济发展。决定这些变革的因素众多,除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外,地理因素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霍维茨列举了大量分析英美地理环境差异的判例,足可佐证。当然,本书关注的核心,还是法律变革中极为复杂的利益博弈。这些利益的主体多元,如联邦与州、立法机构与法院、法院与仲裁机构、法律界与工商界、铁路公司及运河公司与土地被征收或受损的权利人、上游与下游的作坊主、寡妇地产制度中的寡妇与土地购买人、同一河流先后建设桥梁的公司、投保人和保险人、合同(尤其是买卖合同、雇佣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当事人、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与受害人、票据行为的各方当事人……这些博弈不断调适守成与创新、归属和利用、管制和自治、竞争与垄断等相互冲突的价值,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普通私法”规则,如合同法中的合意规则和法定义务并存、财产法中善意购买人的信赖保护、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票据法中的票据流通性等。霍维茨运用的材料主要是法院判决,同时,为了展示决定法律变革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他也尽可能运用了相关领域的材料,虽然这些材料相对不充分。
或许正是因为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书的写法也更为生动。尤值一提的是,它通过大段直接引用和对人物的评价性用语,塑造了一些生动的法律人形象,如法官肯特、斯托里、律师汉密尔顿等。也正因为此,翻译尽可能使用了原文略显繁复的表述,尤其是标点符号,以求保留原文对这些社会场景和历史人物的“想象性重构”。
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可能是对普通法私法规则和司法技术的阐释。本书涉及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票据法、保险法、仲裁法等领域的核心规则,对其形成和变革的缘由,有不少精到的阐释。大量案例也展示了法律拟制、类推方法等司法技术是如何真实被运用的,这些内容展示了霍维茨作为法律史大家钩沉索隐的学术能力、刮摩淬励的学术精神。然而也恰好可能构成阅读障碍,尤其是如本书有关水权和地产权利的内容,脱离英国封建社会的语境就基本无法理解。
翻译本书至今已17年,白云苍狗,时异事殊。十余年前翻译本书时的各种困顿,依然清晰如昨。往者不可谏,来者未能追。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编辑、“雅理译丛”主编田雷教授不弃,本书得以再版。校勘译稿,重温经典,感慨系之。感谢为本书慷慨撰写推荐语的张志铭、郑戈、熊丙万、张泰苏、乔仕彤、阎天诸师友,他们是霍维茨真正的学术知音;也希望本书能遇到更多的中国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