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号:
字号:小
中
大
我学习民法大约已有四十年,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为自己确立了“三个问题意识”,即以中国问题意识、现实问题意识、重大问题意识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出发点和基本目标。这三个问题意识,指引着我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以后,我开始直接参与国家立法的活动,尤其是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更是以这三个意识作为圭臬。树立这三个问题意识后,在分析思考立法问题时,自觉能够打开视野,树立比较大的格局,能够想到国家立法现实问题和大问题,想到人民利益保障的大问题,不计个人物质和学术得失。
在青年时代学习民法我就已经知道,民法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知识性、趣味性很丰富;但是随着学习和研究的经验的累积,我清楚地认识到,民法学科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很强,而且同时也是实践性、现实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习和研究民法不能脱离国情、脱离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重大需求。“三个问题意识”,使我的学习和研究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针对性,一步步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三个问题意识的树立,一方面得益于我本人身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数十年来形成的关注国家现实重大问题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我在学习和研究中一些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
其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国法学尤其是民法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法学理论的混乱给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造成的严重混乱,给我的刺激很大。也就是在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废止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当时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因为新旧理论的混杂而出现了极大混乱。这种混乱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里,一些民事案件的基本分析与裁判规则既违背法理、违背市场经济现实,也无法保障人民重大权利。
我调查研究发现,这种乱象的根源,主要原因是民法基本理论的缺陷,它们不但无法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反而处处添乱。我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本人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不久,首都一家地方法院的领导同志和我交谈时,提到的一个案件讨论会的情形。当时,他们曾经就一个房地产抵押的民事案件召开专家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五个民法教授和专家,居然提出了六种迥然各异的观点!本来,法院组织案件研讨会就是因为法官认识有分歧,因此想借助于专家的知识,统一认识,但是没有想到,五个专家提出六种观点,把法官的认识搞得更乱。
我曾经发表在《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的《中国民法典国家治理职能之思考》这篇论文,也总结了那个时候出现的、在“买卖”这种典型的法律交易过程中、对涉及合同债权成立和物权变动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裁判规则上的七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但写在学者的著述中,而且也写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这种情况,是当时法学理论混乱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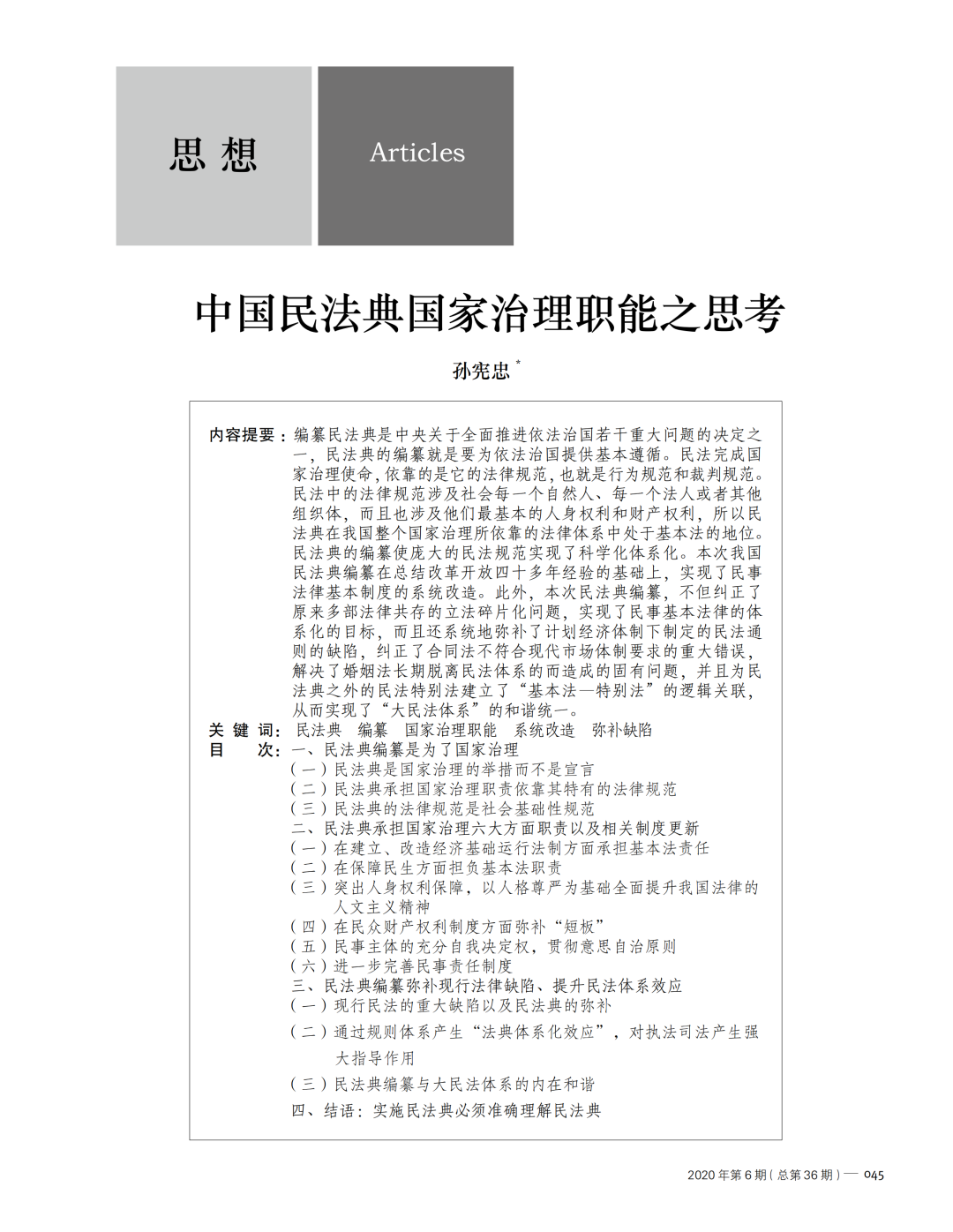
关于合同债权成立和物权变动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裁判,在整个民法的理论和制度建设中具有核心的、普遍的指导价值。因为我们知道,全部法律交易其实都是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的法律问题,也就是涉及合同之债和类似于所有权这样的支配权的转移之间的分析和裁判问题,所以这方面的法律规则,实际上贯穿了全部的民商法制度。可是,如果一个案件,有六种甚至七八种不同的观点来“指导”法官分析和裁判,不难想见,这会给法官造成多大的困惑。
问题是仅仅以我当时学习和接受的民法原理看,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各有各的道理,或者是一个理论的不同侧面而已。从民法科学原理看,这些不同的观点,多数都是有明显的缺陷。有的是和稀泥,有的不顾及民法体系,前后矛盾,连自圆其说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法学理论上的完满和彻底。
2000年初期我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新中国的第四次民法典编纂活动的“失败”,事实上也和我国民法的主导理论混乱有关。当时我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立法专家,多次参加立法会议,对此中前因后果比较了解。这一次民法典编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可以说是下了决心的,法学界也都是积极参与的,舆论界甚至宣告了21世纪要看中国民法典的灿烂礼花。
但是,这一期间召开的一次最为重要的立法研讨会,证明了我国当时的民法主导理论确实没有能力承担民法典编纂使命的客观现实。这次重要的立法研讨会专为民法典编纂召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持,时间是2000年8月,与会立法专家有五六十人之多,讨论延续一个星期以上。会上,学者们不但各执己见,而且提出的观点千奇百怪,根本无法形成共识。
我注意到,本来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民法典编纂”,而编纂就是要将当时已经制定的法律按照科学的体系整合为一个整体,或者说编纂本身首先就要解决体系化方面的问题,但是,恰恰就是这个一开始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却始终很少讨论,甚至不要法典、解构法典、去法典化的呼声也很高。至于我国民法典的编章结构、大量的具体制度、规范的讨论,则更是没有体系和逻辑,大量的观点都是碎片化的。
从这些学者发言中,人们看不到法典编纂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逻辑。所以最后,立法机关只得将当时还有效的几个法律的整体、加上正在制定的《物权法》(讨论稿,尚未形成议案)等等,简单地前后串接起来,形式上成为一个“民法典”(草案)的议案,在2002年12月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一次审议。
这个议案对当时立法的缺陷没有进行任何修正,比如,对《民法通则》第7条关于计划原则的规定,第80条第其中款关于土地不得买卖、租赁、抵押等直接或者间接地否定市场体制、否定不动产市场的规定,也是只字未改(这些条文直到2008年才通过一个打包修法的方案得到了修改)。这个议案的内容和我国当时蓬蓬勃勃的市场经济现实完全不符,稍有法律知识者,都可以看到它的问题,因此它当然无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此后这个议案也就没有再进行过审议。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该议案两年后自然作废。
这一次民法典编纂活动的“失败”给我造成深刻刺激,它让我经常反思我国民法学基本理论的基本法理缺陷问题。我们知道,不要说像民法典编纂这样宏大的立法工程,就是一般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也都是需要科学的法学原理来支持的。但是,那个时期我国民法学的主导理论,只能说是一种以自圆其说为典型特征的实用主义理论,是不具备体系性、科学性的,因此它自然承担不起民法典编纂的历史责任。显然,在科学面前,众口不一、众说纷纭并不是学术的繁荣,法律科学需要理论上的通透和共识。民法典编纂,更不能像一麻袋土豆一样的随意拼装。
那个时期民法学界主导理论的杂乱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如上所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本质转变,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制理论是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都不熟悉的。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法学界包括民法学界都处于封闭状态,对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不但基本无知,而且还长期持批判态度。这样,在我国自己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自己需要市场体制立法的时候,我国法学界包括民法学界的主导理论并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
除此之外,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下的交易观念,也限制了法学界的视野。自然经济的典型,就是农贸市场那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很少通透地思考合同效力以及物权变动效力这些问题,更不会依据法律行为理论上的意思表示来分析裁判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以及物权意思。
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规模大,交易周期长,因此必须在民法上建立清晰的合同债权规则和物权法规则,尤其是要从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这个要点来分析和裁判交易中的权利效果问题。而这些法律规则,那个时候我国法学界包括民法学界很多人都不甚了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5年的“物权法风波”就能知道,我国法学界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产法律规则的理解是多么欠缺。
这一时期虽然国外或者境外法学的引入确实丰富了我国的民法理论,但是因为多方面的局限和法学外语人才的缺乏,再加上引入的方式和理论都显得过于功利,结果偏颇甚多(对此可以参阅本人撰写的《中国民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引进、衰落和复兴》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2期)。这种法学引入,不但不能解决我国民法理论的体系化、科学化问题,反而更加增加了这个时期民法理论的混乱。上面提到的抵押案件讨论会上五个专家提出六种观点之中,以依据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居多,这些观点既欠缺对我国的本土问题的思考,也欠缺体系化科学的精神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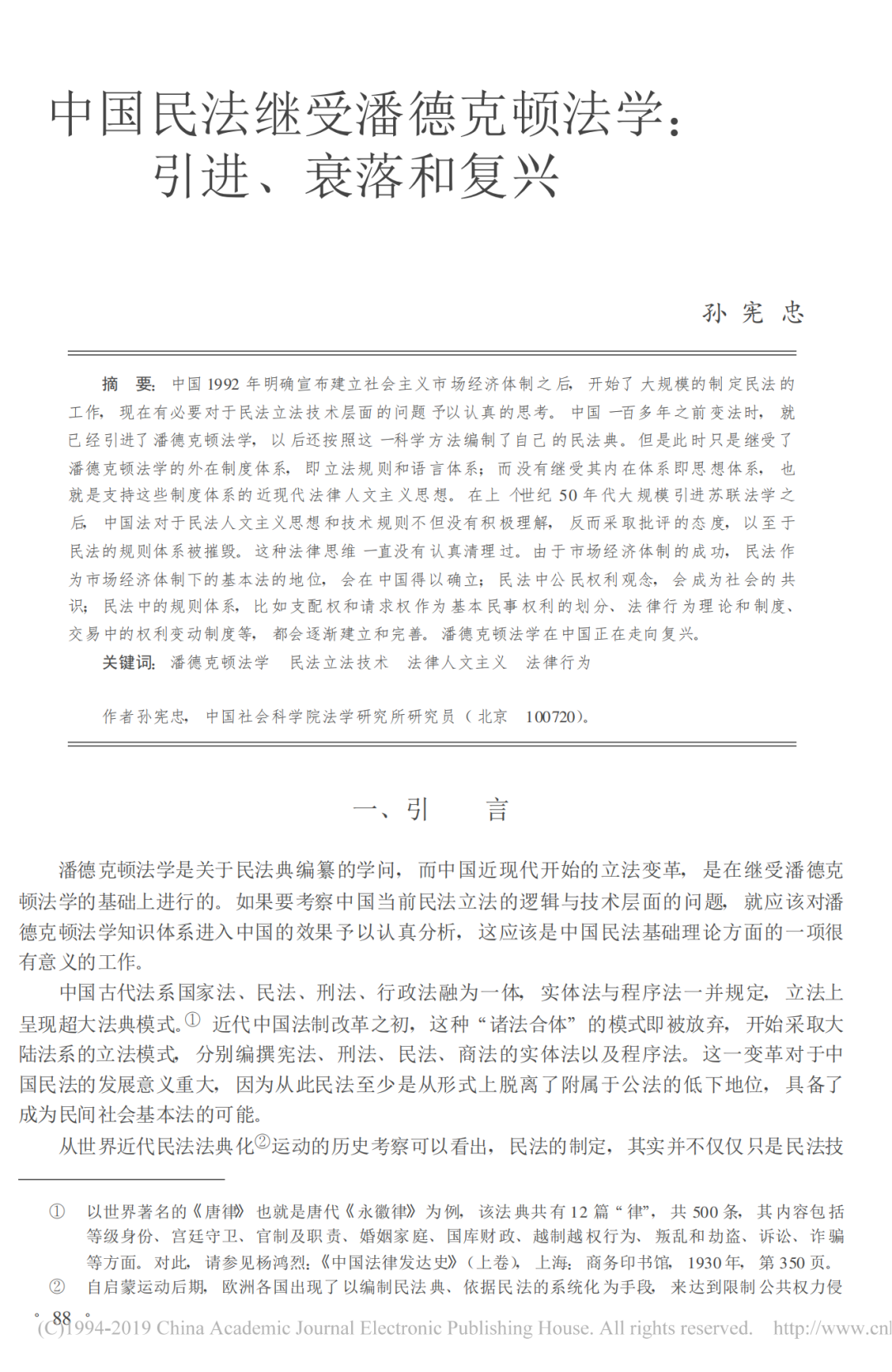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导师王家福教授(已故)的教导启发下,我改变了留学回来后试图以翻译和传播德国经典民法理论作为自己学术工作的研究志向的想法,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民法和民法学术发展的责任,树立了自己的“三个问题意识”。
数十年来,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我不揣绵薄,把体系化、科学化民法学原理和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现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争议最为激烈的物权法和不动产法为起点,对我国民法基本理论的整体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发表和出版了系列著述,形成了初步的既符合民法科学原理、也符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实际和人民权利保障的民法理论体系。
小结一下,我主要的研究努力在于:
一是在民法制度建设的指导理念方面,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事权利观念和民法上的人文主义思想,在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物权法制度方面提出系统观点,一方面强调按照科学民法原理推进公有制财产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在物权制度等方面强化普通民众的权利,逐步消除苏联法学过分强化公共权力、轻视普通民众权利的系统观念,为民事权利确立道德伦理基础和制度保障。这一理念符合中共中央后来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我国立法机关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方面的努力很多已经实现,《民法典》强化普通民众的权利,就是我国民法指导理念发生本质改造的结果。
二是在民法的分析和裁判规则方面,提出“区分原则”理论,贯彻支配权和请求权相区分、绝对权和请求权相区分的基本原理,为法律交易的分析和裁判确立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具有通透科学原理的理论和法律规则。这一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得到人民法院承认和应用,然后在《物权法》中得到一部分体现,最后在《民法典》中得到完全承认。
总之,本人在民法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在近年来的重大立法中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而改造和更新我国民法学基本理论的系统观点,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也为青年一代民法学人普遍接受。
嗟乎!光阴荏苒,四十多年的学术道路真如白驹过隙,求学的道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事情似乎还在当前,却都已经成了过去。有些事情值得记忆,有些事情必须忘记。惟愿我国法律当然包括民事法制,不但在法思想方面能够更加符合民众意愿,而且在法技术方面能够更加规范体系、清晰科学;也希望我国法学事业代代相传,蓬勃发展。
本文改写自作者的《学部委员文集》的后记。
2022年3月11日上午,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旅途中,面对自己的十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我不禁有些感慨,构思一首小诗。这首诗,其实也可以反映我对自己一段学术道路的小结,所以将其附在如下:
旅程,大会堂遐想
一段用时间计算的旅程,
五年,十年,也许终生。
十四亿人的委托,
要用心血来完成。
投票选举、立法、监督,
审议、建言,有赞成也有批评。
举动都是国家的治理,
言谈都代表人民的使命。
这里有时像一池静水,
有时候也是万马奔腾。
这里有时候有无比灿烂的荣光,
也有各种讨论、批评甚至抗争。
来到这里,常常一下子心明眼亮,
有时候也恍恍惚惚,好像在做梦。
国家很大,头绪很多,并非都能理解,
最好,就是埋下头,做好本份的事情。
一年又一年,时光荏苒,
一届又一届,老少替更。
很多人在这里壮怀激烈,
也有人在这里淡淡平平。
有些人在这里步入青云,
有些人在这里堕下泥坑。
我本来只是一个清冷的学者,
我来了,只是为了民法典的使命。
在这里我连续八年殚精竭虑,
议案,建议,立法报告,
七十份建言,
每一次精心准备的审议发言,
坚守学术规范、体系与科学的理性。
天时,地利,人和,
伟大的法典终于完成!
当三千张投票通过的时候,
我在这里热泪盈眶,哽咽无声。
十年里,还有专委会,常委会,
参加过数百个法律的制定修订。
太多条文,太多的记忆,
无数个白天的连续,甚至黑夜,
在这里都能找到踪影。
个人的旅程总有终了,
更多的人会接力前行。
我想说,我付出了我的全部,
我无愧,我忠诚。
国家会繁荣,会强大,
民众会幸福,会安宁。
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
期许后来者,
能够开启更加精彩的旅程。
2022年3月 北京 天宁寺
作者:孙宪忠,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