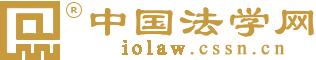字号:
字号:小
中
大
序言:学说状况
在从近代向现代的过渡中,产生了不同的立宪主义,并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不过,这些立宪主义以及辩证关系似乎并不为实证法学说所熟知。
在诸多例外之中,要特别提到的是法学家维多利奥?艾曼奴埃莱?奥朗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公法的“意大利学派之父”),在其1921年至1949年间的各种著作中,他区分了公法的“拉丁学派”与“日耳曼学派”。卢梭的思想是“在学术的方向以及我们拉丁学派的建构中的主流思想”,奥朗多“继承”自卢梭,他把“人格的原始权利”(或者“市民及政治的自由权利”或者“主观的公共权利”)理论以及作为“保障体系”的政制种类都归功于前者,而后者则提出了“专政”的本质,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它被视为单独的主权实体,作为旨在国家规制的客观法的基础,它被理解为领土和全体居民。另外,“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的)思想”创立了“完全不同的种类”,奥朗多将该思想与拉丁及日耳曼(或者德意志)法学派在整体上进行了比较。最后,他认为并提出了罗马法在总体上作为公法的学术发展以及成熟的必要的方法论“模式”。
西班牙比较法学家卡斯坦?托本纳斯(Castán-Tobe?as)也区分了(1956年)“拉丁国家的法与日耳曼国家的法”。
不过,在1969年,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René David)似乎终结了这个问题,他断言在“罗马日耳曼家族内部”区分拉丁国家的法与日耳曼国家的法的所有企图都是矫揉造作、牵强附会的。
相反,自70年代伊始,罗马法学家皮埃朗杰罗?卡塔拉诺(Pierangelo Catalano)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又把拉丁的立宪主义种类与罗马法“模式”联系起来,与这种模式和英国的(其本身所说的“日耳曼的”)“模式”在十八世纪的对立联系起来,罗马模式主要是由卢梭基于法律重新提出并在学理上进行了解释,而英国模式则主要是由孟德斯鸠基于法律重新提出并在学理上进行了解释,以及与不同的立宪主义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这种对立产生并推动了启蒙时代卓越的法律辩证关系。
然后,卡塔拉诺揭露了十九世纪从学术记忆中“抹除”那种对立的企图,这种“抹除”正是通过删除罗马的法律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立宪主义而达到的,而且他还指出并研究了它们在十九世纪自由与独立(不仅在美洲,就这样它变成了拉丁美洲,而且在欧洲)的立宪主义中的“顽抗”,以及在世纪与千年之交“世界的”最后“场景”中对它们的重新提出。
因而,对于当代公法的理解,应当在其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那种产生和适用宪法的特定的同时代现象中,从对罗马法作用的认知开始。这样的理解既给宪法在其形成、存续以及发展前景中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又从公法出发给罗马法本身带来了一种面目一新的解释。
在下面的篇章中,我力图简要地勾勒出一种十八世纪政制辩证关系的理念、其起源及其发展,要注意到的是,很多的(材料上的以及文献上的)忽略不仅是因为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的重构存在很多缺陷,而且还因为对这篇论文在篇幅上的限制。
一、启蒙运动时期立宪主义的形成。对法律科学的共同选择以及法律方面的辩证关系:在历史上“英国模式”与“罗马模式”之间的对立
1、对作为“科学的指导”的法律科学的共同选择以及启蒙时代其它的共同选择
a. 选择法律科学来作为“科学的指导”
这种辩证关系推动了十八世纪的“大革命”以及过渡时代的发展,那么,哪些是该辩证关系的对立概念,在对此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考察它们的共同特征。针对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我认为的三个主要的特征,而根据上下文,按照唯一的逻辑次序,我将其作为那个世纪的三大“共同选择”(这些选择与十九、二十世纪的三大共同选择相对立)指出:α)选择法律科学来作为科学的指导,β)选择公法来作为研究的方位,以及γ)对历史模式方法的选择,相伴地是对乌托邦方法的拒绝。
在十八世纪中,这种辩证关系促进了历史的形成并奠定了所谓的当代的基础,辩证关系首先是通过法律“科学”而建立起来。我特别地强调这个“数据”,因为我认为它常常被忽略了。
十八世纪伟大的理论家(包括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一种“新的(更好的)政体”进行了定义和建构,他们在“自由”中确定了本质的需求,并且为了达到这种需求,他们选择了法律手段,这正如他们主要著作的标题所表达的一样:《论法的精神》(1784)以及《社会契约论》(1762)。
孟德斯鸠拒绝去探究“英国人当前是否享有这种自由。我只要说明这种自由已经由他们的法律确立起来,这就够了,我不再往前追究”(《论法的精神》,XI 6)。
卢梭也没有责任去回应那些批评罗马人行为的人,“我引用法律[…]罗马人是那些不会经常违背他们法律的人;并且他们是唯一拥有如此美好事物的人”(《社会契约论》I 4,注释“a”)。
b. 选择对公法的关注来作为研究的方位
因此,选择了法律的十八世纪的学术天才们选择了对公法的关注。相反,“自由”的问题就变成了“政府最佳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公法的典型问题。
十八世纪是产生伟大“权利宣言”的世纪,并由此开始了“宪法”的创作:也就是那些基本的法律手段的创作,实质上它们是用于(相对于政府)对公共及个人自由的捍卫,这跟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写的(存在着一些在这里不适合深入研究的变化)一样,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进行了重申,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进行了强调和阐释,自那时起一直到我们今天,就由宪法学者以及宪法不断地重复着。
c. 对历史模式的方法的选择以及对乌托邦方法的拒绝
正是为了回答“政府最佳形式”的问题,对于现代思考的起源(也就是,分别始于十六世纪的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olò Machiavelli〉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关注,确定并提出了两种方法(诸模式的方法和乌托邦的方法),在此之间,孟德斯鸠和卢梭还不约而同地对乌托邦方法表示不屑,并且选择了诸模式的方法。
孟德斯鸠批评了“乌托邦主义者”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所使用的对自由的寻找方法,哈林顿是《大洋国》(1656年)的作者,孟德斯鸠批评他忽略了就在眼皮底下的政制模式而去寻求“政治的自由”: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哈林顿,在所著《大洋国》一书中,也曾研究过一国政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度自由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在误认了自由的真面目之后才去寻找自由的;虽然拜占庭的海岸就在他的眼前,他却建造起卡尔西敦。”(《论法的精神》[1748] XI 6)。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哈林顿本应当简单地观察一下四周,在他所在的英国:“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它的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我们要考察一下这种自由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原则。如果这些原则是好的话,则从哪里反映出来的自由将是非常完善的。在政制中发现政治自由,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自由之所在,我们就已经发现它了,何必再寻找呢?”(《论法的精神》XI 5)。
卢梭也表明了自己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山中书简》(1764年)第6篇中,他断言《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被攻击,正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历史上既已存在的模式,而“与柏拉图的《共和国》一起,在空想土地上的《乌托邦》以及《塞瓦兰人》”则是不可丢弃的(这伴有对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以及“空想主义者”德尼?维拉斯〈Denis de Vairasse〉作品《塞瓦兰人的历史》[1677]批评性的影射)。在其《社会契约论》([1762] III 12)中,卢梭写道:“把人民都集合在一起,这是多么妄想啊!在今天,这是一种妄想;但是在两千年以前,这却不是一种妄想[…]我不谈古代希腊的共和国;但是在我看来,罗马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卢梭的政制提议的力度就在于它们的“模式”是有历史证据的,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中首先宣示:“罗马人民[…]所有自由的人的模式”。
2、在历史模式上的对立:英国模式对罗马模式,以及在立宪主义上的对立:代表制(也就是本质上的贵族政治)对共和制(也就是本质上的民主政治)
a. 相对于民主国家的希腊政治经验,共和国的罗马法律经验的特性
α.古代“政制”模式是罗马的法律模式,而不是希腊的政治模式
随着对诸模式方法的选择,共同结束了,对立开始了。
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按照各自提出的年代顺序,这样被确定出来的模式有两种:中世纪(但是其本身说“现代”)英国的(但是其本身说“日耳曼的”)“政制”模式以及古罗马的“人民”的模式。
需要对这种事实进行详细的论述,即古代模式并不是希腊模式,而是罗马模式。这涉及到我所称的“对法律科学的选择”。这种选择更倾向于罗马人,而非希腊人,尤其是倾向于罗马法的共和国概念,而不是希腊政治的民主概念。十八世纪的专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大革命在本质上是共和性质的:“‘民主革命的时代’。它可以被更好地界定为‘共和革命的时代’。事实上,政制的形式以及共和的原则,而非民主,毁灭了旧的君主制度”。实际上,卢梭可以作为榜样,他不仅是一位对罗马共和国(作为“国家的形式”)的伟大解释者和重新提出者,而且,众所周知地,他还表示不赞成民主(作为“政府的形式”),并且尖锐地批评了它的主要表现,即雅典的民主(它没有对两个层次进行区分[参见下面的论述])。对于这个词,西塞罗已经使用了,他批评了由所有人统治的政权(《论共和国》1.26 s)并谴责了希腊共和国完全以集会来实施管理(《为弗拉库斯辩护》7.16)。西塞罗提到了十二表法的禁止,即禁止针对私人起草公法:他们不想针对私人来制定法律,那是特权的意思,因为没有什么比那个更为不公正了,法律的本质是一项适用于所有人的决定或者命令。(《论法律》3.19.44)
β. 在希腊政治经验与罗马法律经验之间的一致以及区别的基本要素
在从“旧政权”的绝对君主制向当代立宪主义的转变中,罗马共和国法律模式的(而非希腊民主“政治”模式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为了理解它,至少需要认真考虑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不仅由在希腊政治经验与罗马法律经验之间的一致性要素构成,同时也由两者之间的区别性要素构成,这不仅是在概念层面上,而且还在制度层面上。
一致性要素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是城市的作用;第二个是由市民所组成的人民(在城市中实施)的权力,这些要素都揭示了“首领”的无用性以及将其变为自己仆人的可能性—合适性。
区别性要素基本上也有两个。
区别性的第一个要素,相对于关于“国家(politeia)”的希腊政治问题来说,正是对关于“共和国”的罗马法律问题在分析层面上的加强。罗马的共和国—法律这一主题在制定法律(之后将被称为“主权的”)的权力和管理的(之后将被称为“行政的”)权力(以及在之后将被称为“国家形式”[共和国或者王国]与政府形式[元首共和国、贵族共和国以及人民共和国])之间做出区分。这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并不允许进行选择(罗马市民不得不成为共和国的人:对于王国的单纯渴望就是一种死罪),而权力的第二个层面可以成为“政治”选择的客体。在制定(技术上:“命令”)法律的(主权的)权力与管理的(行政)权力之间,以及在各自的权力享有者(“由市民组成的人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分工,以新的方式,不仅阐明了由市民组成的人民的权力与管理者的权力,而且还阐明了(居中者的)否决权与作为其权力享有者的保民官制度。在十八世纪,这种模式被卢梭准确地重新恢复了,他提出了在国家和“共和国”之间本质的对立,国家的立法权由代表制议会所行使,共和国的立法权则“实际上”属于由市民组成的人民。因此,在共和国中,可以有政府的不同形态:元首制的、贵族制的以及民主制的。因此,如果孟德斯鸠的立宪主义(众所周知的)完全是贵族制的,那么,卢梭的立宪主义只有通过必要的阐述才能说是民主制的。卢梭使用了用于表示主权形态的“共和国”种类以及用于表示政府形态的“民主”种类,他判断民主“政府”不适合人的本性,并且他倾向于由选举产生的贵族制“政府”:服从人民的命令并受到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作为权利保障的不可放弃手段的宪法性手段,所有的十八世纪关于这个的思考似乎重新恢复了西塞罗(《论法律》3.15 s.)关于作为必要制度的保民官制度的思考,因为“共和国”的确是存在的。
在希腊政治的经验/科学与罗马法律的经验/科学之间的第二个区别性要素是自治市的——仍然是共和国的——创造。正如已经说过的,它是从希腊“城邦—国家”向罗马的“自治市国家”的过渡。罗马法律模式的选择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选择的成果。罗马的自治市,在多个大陆的系统中,伴随着它们对城市以及生活在一起的市民的解决方法进行协调的成果,(如同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观察到的一样)是“我们文明的基础”。
b. 启蒙时代的“英国模式”与“罗马模式”之间的对立及其中世纪和近代的先例
在十八世纪中,在英国的以及罗马的这两种模式之间有着清晰的对立。相反,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是对历史形成以及学说体系进行解释的主要框架。
孟德斯鸠并不限于提出英国自由的模式,他还揭露罗马人作为欧洲自由的敌人:“欧洲长期忍受着封闭且暴力的军政府的蹂躏。然而,大量来自北方的不为人所知的民族在罗马的行省中如洪流般迅猛发展。[……]这些人曾经是自由的。”。
卢梭也不限于提出罗马自由的模式,他还谴责英国人作为对自由一无所知的人们:“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那种方法,也确实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社会契约论》III 15);“我不得不佩服这种疏忽、不谨慎了,而且我敢说英国民族的愚蠢,在他们的成员拥有最高权力之后,设置某种约束去控制他们在7年执行任务期间的使用。”(《对波兰政府的思考》VII)
伴随着(在“城市—共和国”的联盟中重生的)罗马共和国—帝国的古老的自治市制度与(通过对罗马机构[城市—共同体的代表]的移植以及在民族王国“德意志”封建制度中对罗马法因素的移植[《优士丁尼法典》5.59.5.2所提出来的原则:“关涉大家的事”]而建构起来的)中世纪议会制度之间的对立,罗马的以及英国的“政制”模式在十八世纪的对立至少肇始于十三世纪。
对封建制度危机的两种解决方法,即议会制(是对封建制的合理化)以及联合的城市/自治市制(是对封建制的替代),(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而且在空间维度上)都对至今为止欧洲的全部历史打上了印记。
议会制的解决方法产生于西班牙,并推广到了整个欧洲,作为它的一个选定地区,在不列颠王国中对其进行了确立,以至于首次形成了议会的“模型”(1293–1294),议会制度禁止命令式委任,直到我们今天还具有这个特征,这是通过对仍是最新的宗教理论——“虚拟的或/和代表的人”的利用和阐述而引入的。
除了广为传播的议会制解决方法之外,还残存下来广为传播的解决方法——联合的自治市/城市,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联邦的州,它们已经是1241年汉萨同盟的重要城市,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如今,由“联邦参议院”这种同样绝对独特的制度构成其特点)以及瑞士联邦,直到今天,这种解决方法仍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即在欧洲周边,北海的一个岛屿中,产生了英国的君主议会,在欧洲周边——即使有区别地——同样的一个地方,在阿尔卑斯山中,在城市国家的基础上产生了瑞士共和国联邦(1291年),它没有适用意志代表的制度以及州议员通过命令式委任来组成联邦议会,在当时,它是通过之后对代表制度进行修正的一种制度起作用的:公投。
自近代伊始,分别在弗朗索?霍特曼(Fran?ois Hotman:Anti–Tribonianus, 1567; Franco–Gallia, 1573)以及约翰内斯?阿尔色修斯(Johannes Althusius:Jurisprudentiae Romanae libri duo, 1586; Politica methodice digesta, 1614)的著作中诸法律模式的对立是值得一读的;基本的理论分类:一种是英国的议会—国家—君主的经验,另一种是罗马的联邦—自治市—共和国/帝国的经验。
在十八世纪中,这两种法律经验,作为同样在学术上进行解释的历史性模式而被采纳,产生了两种对立的“立宪主义”:不仅是在它们的基本制度上(从公共意志形成的主体和方式以及防止权力来对自由进行保护的制度开始),而且是在它们的基本概念上(从“国家”的概念、“公/私法”的概念、“共和与封建制”的概念以及“民主”的概念开始)。
针对英国“模式”的解释以及相应的“贵族”立宪主义的详细阐释,关于英国议会的法学巨著(尤其是想到了十七世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关于《利维坦—致命之神》以及约翰?洛克〈John Locke〉关于三权分立的贡献)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找到了恰当的概括;之后,还要提到的是,阿贝?西哀士(Abbé Sieyès),第一个关于“代表体系”以及在制宪权与合宪法的权力之间进行区分的伟大理论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共和主义的“英国”版本的阐释者,而且他们分别是各自的“联邦主义”的创造者和理论家,以及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国家-实际的上帝”的哲学家。
在“罗马”方面,对该“模式”的解释以及对相应的“民主的—共和的”立宪主义的阐释,相关的概括可以在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中找到,而关于自治市的作用,特别深入的研究可以在卢梭的《科西嘉宪法草案》(1765年起草,但是在1861年死后才出版)中找到,关于保民官,可以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自然法基础》(1796–97)以及《法律体系》(1812)中找到。因此,并不总是与这个以及/或者那个制度相类似的表现都可以在这些文件中找到,而这些文件则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以及直到我们今天的政治以及制度的创举有关(不过,如今处于不利的境地)。
为了结束在英国政制模式与罗马政制模式之间的“争吵”,邦亚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于1819年在短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比较》中,以他的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该文中,这种辩证的对立被作为一种人类一般“进程”的事件而歪曲了。
3、在概念上的对立
a. 在“国家”的概念上:法人对社团
英国独特的议会制度是建立在与“虚拟的或/和代表的人”相关的概念和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两者都产生于十三世纪(似乎是斯尼巴尔多?德?费尔斯科〈Sinibaldo dei Fieschi〉的著作—《无罪》IV[+1254],这是在教会法的背景下,并且为的是教会法的需要),之后,它们直接在“对命令式委任的禁止”中表达出来,并且在当时刚出现的英国议会法的背景下,以及为了该法(完全的不同:贵族性)的需要,不正常地发展起来了。
“虚拟的或/和代表的人”的概念,抽象的实体,英国议会法的特有事实,是对罗马法的具体实体——“人民—社团”概念的替代,这两个概念分别以针对这样的(我们所能够界定的重要的)法律问题的两个对立的解决方法为基础,即以统一的方式考虑和规制由人类的多样性所提出的行为的法律问题。在公法领域,通过必要地进行“代表”的议会,“虚拟的人”替代了在城市中组织起来的“法律同意和利用的社会共同体”——“整体市民”的“人民”:“因为什么法律支持市民的社团?”
在由市民组成的人民中,共和国作为罗马法的创造,其唯一且必要的所有人、社团以及城市的概念都以此为基础。
与希腊城邦一样,罗马城市(“urbs civitas”)不仅仅是在物理上和制度上的必要技巧,在该技巧中以及通过该技巧,人们在他们之间以及与领土、阶层一起形成了关系,就这样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团体(koinonía politiké,societas civilis)。因此,罗马城市,这次与所看到的城邦相区别,通过社会工具——条约,在向自治市的过渡中,成为一个团体的团体、一个社团的社团的构成要件;甚至因为每个自治市都是一个共和国,所以它们就成为“一个诸共和国的共和国”的构成要件。与城邦相区别,自治市也不能被想象为仅仅是与其它自治市的简单结合:也就是说,与其它的自治市一起,构成了一个更高实体的单位,这样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本身的自治。换句话说,自治市经常被遗忘的特征就是一种统一的制度性逻辑的——内部的以及外部的——两面。
在由市民组成的人民、社团中,单个的“人”是人,而且每个人既是私人,又是公共的人,这就认可将个人的需求界定为并力求达到自身的私人利益,还认可将市民与其他市民一起的需求界定为并力求达到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总是在统一的制度性逻辑中的公共利益(乌尔比安,Dig. 1.1.2)。
1764年,卢梭找到了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求助于罗马法,该问题至今仍然是无法解决的:“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社会契约论》I.6)。
与由市民组成的人民—社团的蕴涵完全对立的,由英国议会经验发展而来的对“虚拟人”建构的蕴涵,在十七世纪中,被托马斯?霍布斯通过“利维坦”(国家—人)的理论化所阐明,它是人们通过一份联合协约而创造出来的实体,在原则上具有“人造的人”以及“致命之神”的图腾崇拜的特征。通过人类不可克服的自私本性(人对其同伴来说是一匹狼)的假设,霍布斯推断出国家—人的必要性,这正是因为它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迫使人们在每个人对抗所有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过程中力求获得个人自己的利益,它阻止了他们为了确定和获得集体—公共的利益而运作:也就是说,阻止他们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过程。不可克服的自私被假设为人类的本性,这源自每个人以及所有“市民”的唯一的私人本性和某个其他人为了他们的集体而思考以及采取行动的必要:也就是说,一个在“由市民所组成的人民”之外君主的必要,因此市民通过一份隶属协约隶属于他。对于这个君主,霍布斯在利维坦的“法人”中进行了准确地界定:也就是(具体地)在其同样必要的代表的“自然人”中,由这样的事实所确定,即规定和行使必要的力量使得自己的规范强加到他人身上。因此,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在正确的意义上,不存在市民(因为根据定义,这些人应当是[其本身的]君主),因此也不存在人民(因为是市民的集合):在他们那里,存在着君主([利维坦的]代表人)与隶属的私人(所有的其他人)之间分裂。
b. 在公法与私法的概念上:分离对区分
随着与私人自然人相分离的君主公法人的创造(替代了对统一的人的区分,人类—市民,他们是社会人民的成员,或者作为私人,或者作为君主),确认了与私法相分离的公法概念,对于这些,我们可以在当代找到。
这样的分离预示着法律归并为私法,因为根据实力这种纯粹的事实性标准,公共关系被抛弃了。事实上,要注意到的是,根据萨维尼的著作,从“伴随着公私法之间纯粹区分的罗马法范例”转向“分离;而且恰当地说法律的领域会限于私法,也就是限于家庭法和财产法”。
c. 在“联邦主义”以及“共和”的概念与“民主”概念上
另一个重要的对立是由“联邦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创造”所造成的,这种创造抨击共和主义的概念。
正如所看到的,罗马模式本质上是共和主义的(罗马公法的重大取舍就是在共和国和王国之间,并且仅仅将共和国转变成王国的“抱负”也是一种苛以死刑的犯罪),而且,在自治市基础上,共和国实质上是联邦性的—社团性的。
这样的共和国概念(在莱茵/汉萨同盟以及瑞士联邦中找到更为有根据的中世纪和近代特有的试验,以及在阿尔色修斯和卢梭的思想中找到更先进的特有的理论化)总是处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以及受盎格鲁撒克逊启发的议会经验和认识之外:孟德斯鸠还不是共和主义者。
不过,在最近的经验中,(通过北美宪法之父们,麦迪逊—杰伊—汉密尔顿)形成了非社团性共和国(共和国=代表制体系)的绝对新的/非正统的(非或者反罗马的)概念,并因此形成了作为共和国特殊形态的“联邦主义”的新词义(以及相应的概念);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对这两个概念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联邦主义是一种晚期的建构,它打破了所有的联邦制传统的先例,将联邦及其历史和教义的对立物结合起来:议会的—代表的国家。因此,它是一种反社团性的联邦主义(以至于除了产生分立而非联合之外,它表现为提出了与所谓的“社团国家”相反的一种功能关系),并且从典型的自治出发,反对共同自治的“政治”作用(以至于它通过在联邦国家与联邦的州之间具体的权限划分而起作用,而不是沿着自治层级的不同程度通过向上的共同参与而起作用的)。
总之,在此之间的对立,即阿尔色修斯在近代所重新提出的罗马模式的“联邦主义”与麦迪逊和康德创新的“联邦主义”,将如同“社团式联邦主义”与“分立式联邦主义”之间的对立一样表现出来。
在民主概念上也确立起一种对立。所有人都会使用在狭义且专有意义上的人民权力的含义,但是这种含义仅仅是由卢梭提出来的(此外,根据西塞罗的模式,也就是说通过对政府权力或者行政权范围的排除,对主权或者立法权的范围进行限制),该含义在十八世纪晚期(特别是这本著作:Jean-Nicolas Démeunieur,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1784–88)已经与广义上的人民权力的含义相对立,也就是与“人民的”代表在狭义且专有意义上的权力的含义相对立;该含义首见于阿雷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中(《论美国的民主》,1835–40)。
在重构之前,对于这部分的总结,正如我们已经详细指出的,需要突出的是,法律的辩证法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对立自其开始时就表明了在英国领域中对罗马领域所采取的制度以及概念的利用—歪曲。这个(不管怎样,它无助于对那种辩证法以及对立的解读)将以重要的方式汇聚到伪概念的扩展以及政治—法律的模棱两可的当代现象之中(在第二部分我们将看到)。
4、在制度上的对立
a. 在公共意志形成的主体以及方式上:国家的议会对在城市—自治市中由市民所组成的人民
在制度层面上,首要的对立已经追溯到了十三世纪,表现在公共意志形成的主体以及方式上,取舍在这两个二项式之间进行:“议会—政治代表”与“自治市/共同体—市民的参与”。
在十八世纪中,孟德斯鸠将英国的政制结构确立为典范,根据他的观点,这种结构所具有的特征是议会享有和行使“立法权”,由“贵族团体”和“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团体”所形成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权”的享有者(也就是“元首”)在一起。与三权分立学说一起,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中的结合,肯定不会有利于在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本质、享有以及行使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事实上,在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中,(直到我们今天)这些权力不断地倾向于合并。
根据卢梭的观点,遵循罗马人民的模式,提出了“社会契约”是“政治团体[唯一的]基础”,立法权的享有和行使应当属于设立它的人民和市民:“人民,服从于法律,他们必须是创造者,它只属于那些联合起来规定社会条件的人”。所有市民在“城市”之中参与他们自己的法律的制定。这就带来了这样的关联,即对代表的议会制度的明确拒绝与一种对作为城市的内在联邦的集合的国家组织的研究。“共和国”是国家的形式,而非政府的形式:相反,这绝对是不可理解的,倘若没有在主权—王权的层级(通过法律来确立权利的权力)与政府层级(执行法律的权力)之间进行明确地区分,这种区分是共和国时期罗马法中在法律方面所进行的合适区分。
b. 在“防止权力捍卫自由的方式”上:三权衡平(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对保民官“否决权”
第二个对立表现在另一个政制的基本制度上:防止权力捍卫个人以及公共自由的权利的方式,取舍是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的,即三权衡平的方式与保民官—市民保护人的方式。
如果代表学说是议会的发动机的话,那么分立或者分离学说以及(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衡平的学说就是制动装置。这样的学说缺少理性的基础,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贵族的—封建的观念提出并构成特点的,它在洛克的学说中找到了最初的理论化,孟德斯鸠对该学说进行了完善。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行政权也分享议会的立法权,这不是通过“管理的权能”,而是通过“禁止的权能”,也就是说“使某些其他人所采纳的一种解决方法无效的权利(droit)”。要注意到的是,孟德斯鸠在对罗马法材料的利用—歪曲的“英国”道路上继续前行,他指出“阻止的权能”作为“罗马保民官的权力”:“[孟德斯鸠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府的基本构造。立法机关将由两个部分组成,通过相互的禁止权能互相牵制。两者都被行政权所约束,其本身也是立法性的”;“在每个国家中,三种权力[…],假如同一个人,或者由重要的人物、贵族或者平民组成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力、执行公共决定的权力以及裁判罪行或者个人之间争议的权力,那么一切便都完了”。
以其一贯的严谨,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III.7中)明确地区分了两种“补救或预防统治者在人数缺乏方面”的“手段”(也就是说,在这两者之间,即“统治者”,意志的掌握者,与“政府”,执行的受托人):“政府的分支”或者“居间的行政官”即“保民官”。显而易见,卢梭并没有将司法活动视为一种权力,也没有为此考虑在统治者的权力与政府的权力之间进行区分。不管怎样,卢梭的立场并非是中立的。他批评了政府的分立,并且提出重新建立一个“保民官”,在人民—统治者和政府之间“居间行政官”:该模式是罗马的保民官。
这第二个对立是最近形成的。自近代伊始,它才突现出来,并且作为改革的后果,当天主教教会统一的崩裂,损害了主教任命的城市保民官的作用,它强制性地重新提出了针对统治者的对被统治者保护制度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近代首要的解决方法——已经从十六世纪开始——在平民保民官的罗马模式中重新找到,不过,这里的学术记忆以及对制度的重新提出也在先前的世纪中表现出来了。因此,那种解决方法与出现在议会范畴的分立或者分离以及三权衡平的学说相对立。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5月10日著名的《关于宪法》的演说中,在“对抗政府本身保护个人与公共的自由”中,指出了“所有宪法的首要目的”,通过对政治家设想出的“两种达到此目的的方式。一种是权力的衡平,另一种是保民官”的确认,他概括了这种对立的状况。
c. 在异常情况与平等上
关于公法制度,在“公共意志形成的主体以及方式”上的对立以及在“防止权力捍卫自由的方式”上的对立都是本质上的对立。此外,它们并非是仅有的。至少还需要提到的是在“独裁”职位与“监察”职位上的对立。
关于为了应付异常情况的制度,罗马的独裁制度(卢梭:《社会契约论》,IV.6,“论独裁制”)与英国的中止对政府限制的制度相对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XI.6:“如果立法机关认为由于某种危害国家的阴谋或者通敌情事,国家已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它可以在短促的、一定的期间内,授权行政机关,逮捕有犯罪嫌疑的公民;这些人暂时失去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由于永远”)。
罗马的监察制度是为了达到公民之间的平等而通过道德习俗的保护做出规定的(卢梭:《社会契约论》,IV, 7,“论监察官制”),它与在古代人的“道德”和现代人的“恶习”(作为反对平等的标志,与崇尚奢华联系起来)之间“价值”的对立相关,该制度被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所痛恨。
二、罗马模式的“拉丁”立宪主义的克服阻力(与抵抗)以及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和国家形态的优胜:同时代中期法律辩证法的中断与法学的危机
1、从反对1793年宪法的法国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政变,到取消这个模式的企图:罗马公法
在罗马政制的模式—体系与英国政制的模式—体制之间十八世纪的法律辩证法,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迅速脱离了血拼。第一部仍为君主制的宪法(1791年)毫无疑问地定位于英国模式(因此是坚定的代表制—议会制),在此之后,在1793年之间,产生了两部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对立,一部是(仍为英国模式的)吉伦特派草案,一部是(罗马模式的,因此是参与性的—自治性的)雅各宾派草案。在大会中,雅各宾派草案占据了上风,它形成了第一部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31年,卡雷?德?马贝格(Carré de Malberg)将其界定为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民主宪法,因为它没有堕入到对人民主权在理论上肯定和在实践上否定的矛盾之中,而这却是同时代其它宪法所具有的特征。
1793年宪法(它在实施立法活动和实施政府活动之间采取了严格的分离,这根据的是它们之间严格的概念区分)规定了在一个“立法机关”中聚集的“议员—代表”,立法机关叫做“国民大会”,但是议会不能在没有公民意志参与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该宪法并没有仅限于宣布:“主权属于人民”(《权利宣言》第25条);在第10条中,它简洁明确地规定了“对法律的审议”(参见第19条)。被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只能“提出法律”(第53条),因此“草案”被“印发于全共和国的各市镇”(第58条),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第59条所规定的方式,如果“有异议,立法机关应召集初级会议开会”(第60条),为的是对所提议的法律进行议定。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宪法》的著名演说中已经告诫道“在初级会议中要特别注意主权的自由”,并且在1792年结束君主制的国民大会中,在该宪法之前有一系列卓越的宣言或者有这些宣言相伴,以联邦为关键,这些宣言旨在具体地在(小)市镇中确认人民主权的典型地点。这也包含着实现对“法律”数量进行严厉限制的古老且总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目标。
此外,1793年宪法承认(《权利宣言》第33-35条)这些是合法的,即“反抗权”与“人民及一部分人民”在“受压迫”情况下的“起义权”。罗伯斯庇尔也确认了它们只能在“捍卫权力自由、权力衡平以及保民官的这两种方式”中找到,他不想或者不知道([卡塔拉诺认为的]可能由于理论阐述的不充分)通过完善对人民授予保民官的权力在自己的宪法中加入保民官。相反,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在政治上重新采纳了保民官的概念,并且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学术上以“根据自然的合适状态”为基础对此进行了发展。
根据卢梭的观点,它是罗马公法的模式。
针对1793年的共和国宪法,产生了斗争。雅各宾派还通过“恐怖政策”捍卫了革命的选择。反对派通过热月9日政变以及随后的镇压终结了罗马政制的试验。
最终,拿破仑后来的共和国—帝制的试验也失败了(滑铁卢,1815年6月18日)。
罗马模式的法律—政制体系的不幸是与“罗马派”的政治军事的厄运相一致的,可以确定的是英国模式的法律—政制体制与此相对立。1795年的宪法重建了英国模式,它正确地反对了1793年宪法,旨在“缩减民主”。这样,法国的两个宪法学者是法国宪法评论文集的作者,他们观察到:“然而,在1793年,我们试图发展民主,到了1795年,我们缩减它[……]反民主的宪法[……]就人民来说,选举人明显不信任[……]公民投票也被取消了[……]宪法于1791年为了权力分立而制定出来”(德巴什—波蒂埃:《法国宪法》第2版,1989)。
英国模式立宪主义在政治—军事以及制度上的胜利伴随着在学术上对罗马法律—政制的模式—体系的涤除,错误地造成并繁殖了“民主的”共和思想。
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法学家,尤其是最重要的:德国人(仍然全部是“罗马法学家”,但是却被古罗马法律—政制的模式—体系的“幽灵”所“恐吓”),通过对公法构成要件的准确抨击,提出了驱除那个“幽灵”的目标。公私法的分离为这种“抨击”做了准备,它做出了有利于私法的选择,并且达到了对罗马公法的(模棱两可地学术性:因为是在学术材料的基础上学术性做出的)否定。这种抨击是在一个世纪中以一种几乎机械的重复而确立起来的,我们能够对这种抨击的各个阶段十分概要地做这样的梳理:
α) 1835–1849,从安东?弗莱赫?冯?哈伊姆伯杰(Anton Freiherr von Haimberger)到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Friedrich von Savigny):从宣称罗马公法的“不纯粹”到宣称罗马公法的“不合时宜”;
β) 1871–1893,特奥尔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罗马公法特质的毁灭(以“Staat(国家)”这个词来翻译罗马文本中“populus(人民)”这个词,确认了“罗马公法[……]如同每一种法律都对国家做出假设一样”,确认了人民/国家的权力是由其代表人行政长官 “带来”的,他们没有从作为市民的人民那里接受权力,而是他们向众人传达它,因此,宣称罗马共和体系以及拥有“否定权”的保民官并不具有特性,而且还从“罗马公法”中去除了市镇组织);
γ) 1889–1934,从奥托?莱内尔(Otto Lenel)到弗里茨?舒茨(Fritz Schulz):从《市民法的重生(palingenesia del ius civile)》基本上对罗马公法的忽略到宣称罗马公法的不存在。在二十世纪中,主流法学的结论,即否认在罗马的“法律体制”及其本身的学术阐释中“公法”的存在,这是荒谬的,直到今天,这种结论的影响力仍然在对概念以及“政治”组织的运作之中占优势。
2、罗马模式的国家形态的抵抗与“拉丁”立宪主义的形成
a. 自由与独立的拉美立宪主义
即使在十九世纪政治及学术进行反对的背景下,罗马模式的立宪主义并没有消失。它与成为“主流的”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之间的——不再平等地辩证的——关系变成了——就它的视角来看——“抵抗”。
在这种抵抗中,“拉丁”化美洲独立的发起者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仍然是在十九世纪中,“罗马的”—“英国的”在法律上的对立,特别是被“英国的”著作解释成“罗马的”—“日耳曼的”在法律上的对立,遭到了重大的变革,为的是在法语的词汇以及概念中引入“拉丁人”的种类,通过这种引入,学者们,诸如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以及朱力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拉丁人”的新的种类中“超越”了在“高卢人—罗马人”与“法兰克人”之间数百年来关于国内的—法兰西的“争论”。这个新种类有力地进入了对伊比利亚影响的美洲次大陆本身的一致性研究和定义的过程中了。这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中(近来仍然思索对本土成分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在名词“美洲”与形容词“拉丁的”之间的关系并非具有唯一的意义,因为,就它看来,这个美洲突出了“拉丁的”观念:尤其是在其对“罗马的”概念以及法律维度进行重新操控的意义上。
拉丁美洲独立的发起者明确地采纳了罗马模式的立宪主义,并且采用了那种模式的特有制度:首先是自治市与保民官,还有监察官——道德权力与专政。仍然是出于所说的理由以及根据所说的标准,现在我限于对自治市和保民官说些简短的题外话。
在1798年、1801年和1808年,佛朗切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起草了三份宪法草案,它们以联邦的形式在由城市所呈现的组织核心(“议会”、“市政厅”)的基础上创作出来。对雅各宾派“中央集权制”的——广泛传播但却错误的——确信,似乎使得这个是出人意料的,即“米兰达草案充满了法式理念,它也提倡一种平民的和联邦主义的观点,组成作为自由的自治市联盟的西班牙裔的美洲(斜体是我写的)”。
在拉普拉塔河省宪法草案中(1811)规定了保民官制度。
因此,出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原因,特别有意义的是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学术思考以及立法建议的贡献。在这个特有的政制思想中,在体系上参照了当代英国的模式以及古罗马的模式,为的是赞同罗马法,得出他所界定的“全部法律的基础”以及他所推荐的研究。在安哥斯图拉议会的开幕词中(1819年2月15日),从对英国政制中“权力的分立和衡平”的支持出发,玻利瓦尔已经注意到“罗马政制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权力和财富。在此没有对权力的精确划分”。在玻利维亚的制宪大会的演讲中(1826),在此更清楚地从支持古罗马法律体系出发,他叮嘱道“记住,立法者,国家由城市和乡村组成,这种安宁乃国家之福”。在巴拿马会议中(1826年6月22日—7月15日),玻利瓦尔提议美洲共和国的永久的联盟、联合以及同盟,这构成了玻利瓦尔政制学说的基本资料。在玻利维亚宪法中(1826),玻利瓦尔在第26条中引入了“保民官会”。
在1824年巴西的帝国宪法中,由该宪法的主要编纂者约瑟夫?约阿金?卡内罗?德?坎普斯(José Joaquim Carneiro de Campos)加入了“居间权力”,这相当于保民官的权力。
1833年,“平民保民官”被加入到了由秘鲁人曼努埃尔?洛伦佐?维达尔(Manuel Lorenzo Vidaurre)编纂的宪法草案之中。这个人是秘鲁共和国最高法院的院长,也兼任巴拿马大会美洲会议的秘鲁共和国全权公使。该草案的第49条规定“应当有名为平民保民官的部门”。后面的条文,直到第69条,规定了该制度。该草案还伴有一份复杂的且十分有意义的阐释性演讲,批评了国家的法律拟人化以及三权分立,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了五权分立:选举权(主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保护权(“保民官”的权力)。
几十年后(1874年),在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州还设立了“穷人维护者”。
不久之前,阿根廷宪法学家以及制宪者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朝圣或者旅行的黎明与在新世界中的真理冒险》,1871年)已经在(他界定为“议会的”)“英美现代自由”与“古罗马—拉丁的自由”之间的(他界定为“种族的”)选择中发现了美洲政制的窘境。
古巴共和国独立之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在1891年的一份手稿中)解决了这个窘境,在罗马自治市制度中指出了“属于我们的美洲”的自由的基础和生命:“自治市是最稳固的文明,来自自治市的[...]大部分西班牙殖民者,大部分殖民地,进入了美洲的自由。这是自由的基础和意义:自治市。其所具有的特征是研究公共事务并参与其中。权力的日常使用,对此可以单独地检验,并且防止它们以保护人民”。
此外,值得提到的是,乌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尔纳多?普鲁登西奥?贝洛(Bernardo Prudencio Berro)(1860–1868),在“自治市制度的必要性”上的贡献,这些贡献围绕的是1861年其著名的法律草案(正是关于“自治市制度”)。
b. 自由与独立的欧洲立宪主义,特别是意大利的例子
在欧洲环境下,我们也找到了重新提出监察制度和专政制度的例子,但是这里我也仅限于对自治市—联邦制度以及保民官制度的思考。
在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家们的贡献,他们都处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广阔且不同种类的领域之中,不仅涉及到联邦的地方自治主义,而且还涉及捍卫公民—劳动者的制度手段。法国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联邦的原则与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1863年)和俄国人米哈伊尔?亚利山德罗维奇?巴枯宁(Michail Aleksandrovic Bakunin)以及皮埃尔?阿列克谢?克鲁保特金(Pierre Alexievitch Kropotkin)支持“自治市的联邦”。1871年,巴黎宣布国际工人运动。1906年,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启发,《亚眠宪章》宣布了工会在制度上的自治权以及它在政治上对左派和右派的脱离。在这些年里,“工团主义者”,诸如法国的让?阿雷曼(J. Allemane)(1900年)以及美国的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éon)(1903年)指出了罗马保民官作为工团制度的先例和模式。
1845年,在意大利,更为独特的是,江?多梅尼科?罗马尼奥斯(Gian Domenico Romagnosi)(《民法哲学教科书,即理论法学教科书》)对明显受罗马所启发的“国家”组织体系进行了理论化,该体系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存在着一种作为“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法定的中间机构或者权威机构”的“保民官”。
仅仅在四年之后,即1849年,(通过加里波第〈Garibaldi〉和马志尼〈Mazzini〉)在罗马重新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在此我们找到了由凯撒?阿国斯蒂尼(Cesare Agostini)编纂的宪法草案,该草案受到罗马模式的强烈影响,(此外)它不仅表现出赋予了自治市的作用,还表明了保民官的存在,对此,卡罗?卢奇阿诺?波拿帕德(Carlo Luciano Bonaparte),罗马制宪大会主席,确认了:“保民官是我们这个政治构造的关键、主要支柱”。
关于自治市的自治作用以及我们的联邦关系的问题,在现实的“共和国”组织中,被不断地重新提出。在1849年罗马共和国之后,我提到在意大利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维谦佐?吉奥贝第(Vincenzo Gioberti,1801-1852)、安东尼奥?罗斯米尼?索巴第(Antonio Rosmini Sorbati,1797-1855)、尼科洛?托马塞奥(Niccolò Tommaseo,1802-1874)、卡罗?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1801-1869,罗马尼奥斯的弟子)、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1811-1876,蒲鲁东的朋友)、朱塞佩?蒙塔内里(Giuseppe Montanelli,1813-1862)、卡罗?比萨卡内(Carlo Pisacane,1818-1857)、以及——首先是——皮埃特罗?艾雷罗(Pietro Ellero,1833-1933)对此的贡献。艾雷罗,法哲学家和刑法学家,撒丁王国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批评了源于英国的“代表秩序”,并且颂扬了源于罗马的自治市及保民官制度(《资产阶级专制》,1879年,界定为“最绝妙的人类制度”)。艾雷罗的作品(他在“罗马人”和“拉丁人”种类之间确立了连续性关系,并且,正如朱塞佩?布里尼(Giuseppe Brini)将提到的一样,他主张“重新提出罗马公法”),关于意大利的公法思想,相对于约翰?卡斯帕?布伦特斯克利(Johann Caspar (Kaspar) Bluntschli)(以及鲁道夫?聂斯特Rudolf Gneist的)作品所提出的视角,建构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参照点。大约在艾雷罗同时代中,“撒丁岛反君权者”焦瓦尼?巴蒂斯塔?图维利(Giovanni Battista Tuveri)(教士和政治家)是自治市的“政治”作用的支持者,他捍卫了皮埃蒙特政府。
在意大利的国家形成阶段之后,对地方的(以及在较低程度上,联邦的)自治主义的鼓吹在意大利并没有消失,尽管维多利亚?艾曼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通过伯爵加富尔〈Cavour〉大臣以及拿破仑三世军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作用)对除了半岛之外萨伏依王朝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定。在二十世纪中,路易吉?斯图佐(Luigi Sturzo,1871-1959)也是教士和政治家(除了长时间在西西里是卡尔塔吉罗内市政府的成员,还是“人民党”的建立者和众议员),按照一种联邦的逻辑,通过确认相关市镇的(以及地区的)基本作用,他对“人民”自己的选择给出了制度上的意义。1920年,另外对于意大利国家战后危机的非法西斯的解决方法——《卡纳罗宪章》,也“赋予了自治市以广泛的功能”,通过这些功能,可以追求实现“直接的民主”。
二战之后,焦乐乔?拉?皮拉(Giorgio La Pira,1904-1977),是罗马法教授、立宪会议成员、佛罗伦萨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对市长的职务与同样的罗马法的种类——(在这个背景下,界定为命令式的)“委任”进行了比较。拉?皮拉在自己的佛罗伦萨市长职务卸任演讲(1964年)中写道“人们可以自由地不接受委任;然而,如果人们接受了委任,必须完成之[…]”(引自优士丁尼法学阶梯I.3.26.11)。拉?皮拉特殊的功劳就是将“自治市”与超国家的视角和维度紧密地联系起来(1955:罗马首届“资本主义世界市长大会”)。拉?皮拉的贡献值得予以特殊的关注。他将罗马法作为现行甚至有效的法律来研究和教授,这正是从罗马公法出发的,尤其是从这两种共和主义的制度出发,即自治市(通过市民城市的社团/联邦体系)以及——以含蓄的方式说——保民官的权力。基于此,拉?皮拉并不限于否认国家具有消灭城市的权利(吉奈弗拉的演说,1954年,“城市的价值”),也就是消灭城市,因为在城市中,也只有在城市中,才留有市民,人类社会的根本支柱。为了整合国家,需要整合城市(巴黎的演讲,1967年,“为了统一国家而整合城市”,列宁格勒的演讲,1970年,“为了整合国家而整合城市”),为了挽救国家,需要挽救城市(都灵的演讲,1971年,为了挽救国家而挽救城市),他对此进行积极的理论化。不过,今天我们在“全球化”或者“世界化”的现象中发现了世界的诸问题制约着单个国家以及单个城市的管理,拉?皮拉,年逾50,天才般地(预言式地)推翻了该问题的界限,提出从“市民城市”的内部并通过“市民城市”特定的方式来处理世界问题,因此,将“市民城市”的问题作为世界问题,而非一般性问题进行处理。
c. 英国和罗马的政制模式与美国的“南北战争”
在罗马共和国的同时代,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一个北美的法学家—政治家,这个次大陆的伟人之一,并且今天为人所熟知,与制宪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一起,作为北美立宪主义的另一个伟人,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也提出了两种政制模式的存在:英国模式与罗马模式,而且他还推荐具有保民官权力的特色的罗马政制模式。卡尔霍恩的两部巨著(《政府研究》和《美国的宪法与政府的研究》)写于1848—49年间,但是死后才出版(卡尔霍恩死于1850年),这两部巨著从根本上分析了罗马的“政制”模式,并建议在北美的联邦体制中加入一种“保民官的或者否决的权力”,在美国联邦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受到北部诸州优势所威胁的政制衡平,要重新采取那种模式。发生在1861年至1865年之间的北美内战,也被准确地称为“分裂战争”,因为——根据卡尔霍恩的理论——建议重新确立古代保民官的权力,这种抉择追溯到了对古代平民的分裂。正如所看到的,该“模式”是被“严肃地”采纳了。
在分裂战争结束后的一些年,意大利法学家圭多?帕德雷第(Guido Padelletti)(《政治选举原理》,那波里,1870)写道:“罗马的伟大开始于那个时期,即圣山分裂产生了保民官。美国宪法基于多数人的权力,忽略了将此永久地置于监督之下,所有的权力都需要它”。
3、作为唯一形式的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的优胜:“国家集权主义”,利用了法学的术语-概念的模棱两可与危机
随着罗马模式的消失,并且在其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对立宪主义的认知能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对罗马公法的放弃使得缺少了法律的辩证关系,而在十八世纪中,这种辩证关系曾顺应了对“政制革命”的孕育,并启动了从“古代制度”向当代过渡的进程。
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国家集权主义,因为它使国家人格化,尽管这通过的是其“代表”(议会)的功能,变成了“国家集权主义者唯一的思想”。替代在对“国家”明确地界定且对立的两种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要对国家的“英国”模式进行确认,而且还要对此进行确认,即国家—利维坦,(必然)被代表的法人,它变成了已知的唯一的国家模式,这并非出于人类所有的历史而可以想到的唯一的国家模式,即使这同样地要求人类要“逐渐地”完善它。
这种唯一性的思想导致了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占优势的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性要素:法律术语的,尤其是政制术语的模棱两可。英国模式的唯一的国家形式,在清除了自己对手的痕迹之后,为了给自己“贴上标签”,使用了逐步涤除对立模式的名词,这样就“完善了”数百年来将罗马模式的国家形态的特有概念占为己有的实践。人民主权与议会主权相协调,共和国转化为代表的体系(通过各种可能的“联邦主义者”:麦迪逊—康德),民主在没有实质区别的情况下被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德梅乌尼埃乌—托克维尔),人民变成了利维坦(鲁比诺—蒙森)等等。结果就是——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了——概念的混淆以及“相应的”词语含义的丧失。
法律辩证关系的缺乏以及对国家集权主义者唯一思想的确认,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法学划时代的危机以及对其科学的指导角色的撤销。
缺乏这样辩证关系的首要后果就是罗马法学的危机,该法学是建立在公私法特有的互补性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罗马法的根本特征不仅仅是公私法之间的区分,而且在这种区分中,两种概念相关的地位并非是相同且无差别的:所描述的概念正是“公共的(publicus)”概念,而“个人的——私人的(privus–privatus)”概念仅仅指某人以及/或者某物不是“公共的(publicus)”。
第二个后果就是所有法学的危机,在十九世纪中,法学将科学的指导角色让位于新生的经济学,它承担了建构一种新的辩证关系的责任,并将法律降低为经济学的一种“多余的附加物”。
4、(通过乌托邦方法)选择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指导以及拒绝了历史诸模式的方法
当代经济学新的伪辩证关系的前提已经在十八世纪的法学辩证关系中找出来了,特别是在善恶的对立中找到。然而,亲罗马的阿贝?德?马布利(Abbé de Mably)将一种在散发着恶性与奢华的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赚钱”文化视为“矫作的”、失败的。亲英国的西哀士,针对民主,将“代表体系”的必要性建立在民主之上,而他将民主确定为现代经济学典型的特征(引用了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鉴于财富的增长而对功能的划分(partage des fonctions)。1819年,邦亚曼?贡斯当重新提出了与西哀士相同的观点:取代由所有公民对权力的民主参与所保证的自由,才存在商业的自由。在法国,新的宪法的第一部“手册”是邦亚曼?贡斯当的《宪法政治教程》(1818-19,之后由爱德华?拉宝拉耶(Edouard Laboulaye)于1851年和1872年进行注解和编辑)。
实际上,苏格兰启蒙运动学派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它具有以固有的或者内在的“法律”为基础的特征。作为“市场的法律”,新的经济学要求对生产性功能进行划分。如今,尽管这可能看上去是荒谬的(这是因为,这些今天被视为思想之父以及自由实践之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者们所具有的各种表现:自由散漫主义、自由贸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但是,正是从它们身上,“英国模式的宪法学家”得出了集权主义者以及等级主义者组织的需要。
在十九世纪,在先驱者圣?西蒙(Saint Simon)和路易?勃朗(Louis Blanc)之后,首先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相对于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关于一种新的经济学伪辩证关系,他针对“苏格兰人的”观点提出了必要的对立命题。另外,马克思取代了(古老的和法律的)历史诸模式的方法,与孔多塞(Condorcet)和贡斯当一致地宣布了它们的终结,坚决地选择了(经济上的)乌托邦方法。
三、法律问题的当代回归:“国家危机”和“宪法不存在”的学说;罗马模式的国家形态的自发重现
1、近来关于“国家危机”的学说,但实际上是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与立宪主义的危机
a. 近来关于“国家危机”的学说及其局限性:同时性(缺少对“结构”部分的认知)与历时性(缺少历史的—系统性的解释)
法律的思考,以及更一般地“社会科学”的思考,在近些年来,为了阐明“国家危机”的种类,都具有一种学说性拓扑思考的特性。
该学说正确地利用了“危机”的种类,用以说明一种持续性中断现象以及过渡现象,因此:在没有价值评判的情况下,这不仅有先在状况的变质以及消失的方面,我称之为“消极的”方面,而且还有新情况的突然发生以及强迫接受的方面,我称之为“积极的”方面。
特别是,该学说正确地将中断以及过渡现象的全部解释为“国家的危机”,而这些现象冲击着同时期的宪政国家。
罗马法学者也利用公法来作为研究立场并采纳了刚刚提到的解释模式,不过,就罗马法学者看来,该学说在对该危机的解释中表现出了严重的局限性。
它有一种“同时性”的局限,也就是仅限于国家危机的“表面的”部分。事实上,还存在着国家危机的另一方面,该方面当然并非是不重要的:即“结构的”部分。
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历时性”的局限,这与另一个局限是相关联的,它没有感知到这样的关系,即如今现象的连续性与在“国家形式”以及相关联的立宪主义之间十八世纪以及十八世纪之前的辩证对立的关系,以及与它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些局限开始就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因此甚至成为(至少在所谓的“西方”法律文化和实践中)当代仅有的局限,它们的全部就使得该学说将国家的一种形态(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也就是一种立宪主义(相应的立宪主义)的危机的一部分(表面的部分)称为“国家的危机”。
b. 近来关于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和立宪主义的危机:外部和内部以及“表面”部分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
同一国家的内外维度在过去是绝对不可渗透的,国家危机的表面部分(或者更好地: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危机的表面部分),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各份权力有影响的互相渗透,而对权力进行划分在过去则是国家的唯一特性。
那么,这部分危机的消极方面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重大削减。
因此,其积极方面就是对新的权力“中心”或者“主题”的建构,这不仅要针对国家维度的外部,而且还要针对其内部,而这些不是或者似乎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国家的本质。
这分别涉及到的是,针对国家外部的所谓的“全球化”进程,针对国家内部的地方机关(首先就是城市的)政治角色的要求收回—承担的进程。为了全面界定这两个进程的全部,就创造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zazione)”这个词语。
这种对“国家危机”表面部分的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正如预见到的,它有这样的缺陷,即在该部分范围之中,没有感知到如今危机的连续性与在“国家形态”以及立宪主义之间十八世纪以及十八世纪之前辩证关系的对立,以及与它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的解释模式允许在今天的全球化中(绝对不能与罗马的一般主义相混淆,然而常常会这么做),承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集权化进程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则是罗马政制模式重新产生的相反进程的一种表现,综合看来,这两种进程都是在我们讨论的选择模式之间辩证以及碰撞的表现。
为了从“国家危机”的流行但有缺陷的视角转向“国家的一种形态的危机”以及相应的“立宪主义的危机”的视角,在性质上对在全球化进程与城市重新获取政治角色的进程之间进行区分则是第一步,除了纯粹的“表面的”部分之外,还要通过对“结构的”部分进行弥补。
c. 近来关于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和立宪主义的危机:基本制度和根本概念以及“结构”部分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
于是,该学说以组织的方式(尽管伴随着历时性感知的缺陷)指出了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危机的表面部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该学说倾向于将部分等同于全部,忘记了这种国家形态的危机当然并非不重要的另一个部分:我称之为“结构的”部分,因为它不仅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变体之中(从公共意志的形成制度以及对自由的保护制度出发,仍然在国家的这种形态中,这些制度是政治代表制度和三权衡平制度)冲击着国家的这种形态,而且还在相应的立宪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中(从“国家”以及“共和”的概念本身出发)冲击着国家的这种形态。
危机的这个部分也有(如今主要制度和概念的变质和消失的)消极方面以及(“新的”以及不管怎样对立的、替换的制度和概念的突然出现和强迫接受的)积极方面。
“结构的”部分通常忽略了涉及关于“国家危机”主题的学说,这样的事实显然并不意味着该学说对于国家的必要且基本的政制制度以及概念的危机并不感兴趣;相反,这样的观察是重要的,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危机的结构部分的积极方面,除了专门经验性的之外,大部分都是本质性的,与此同时,消极方面,除了专门经验性的之外,大部分也都是本质性的。正是这种观察,才能补全我们将“国家的一种形态的危机”以及相应的立宪主义的危机解释为“国家的危机”:不过,这是通过在国家形态与立宪主义之间的相反关系完成的,根据的是我们提到了危机的“结构的”部分的消极方面或者积极方面。
然而,该学说研究或者直接地提出这样的危机现象,它不仅没有与关于国家危机的作为一个整体另一部分的(表面部分的)学说镜像般地联系起来,而且通常也没有在其整体中抓住“结构的”部分。事实上,它们的讨论客体不仅与每一种不同的制度和/或概念的危机无关,而且与全部现象的各自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无关。正如所宣示的,我用复数写“宪法不存在”的学说,就是这个理由。最后,还是关于危机的“结构的”部分,不同的学说以及全部学说的规则并没有抓住我们所面对的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以及立宪主义的制度和概念的危机,也就是,在十八世纪中,理论化以及提出的两种国家形态和两种立宪主义(另外的是罗马模式的)之一的危机。
不过,可以并且需要在这两个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但同样重要的流派中区分以及整合不同的学说:1)在法律上更恰当的流派,源于“罗马——日耳曼的”流派以及2)主要在政治学上的流派,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流派。
对法律的思考以及政治学的思考的接触、时间以及结果,在它们之间,似乎在年代上是相异的,在实质上更是不同的。
然而,法学家的思考,相对于政治学家的思考,在某些更久远的方面以及在其它最近的方面,对于所说的“封闭的空间”,不仅倾向于分开考虑处于危机中的各种制度和概念,而且大多会仅仅止步于破论部分,也就是仅仅对危机的消极方面进行考虑。通过对危机两个方面的总体考虑,向立论部分的转化,并不是由这种学术思考所进行的:这不仅是因为英国模式国家集权主义者思想的单一性,并不允许承认有合适替代的可能(也不允许对其制度进行批判的法学家),而且还因为与之相关的罗马法律模式在学术上的灭失,不管怎样,都不允许积极地去看待这种替代物。
并没有背离(相反,以某种程度确认了)已经做出的这样的观察,即关于危机的结构部分积极方面的经验占优势的(也就是它既没有由学说提出,也没有被学说进行突出)本质的观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确认的是,政治学的思考缺少学术模式(之后,在今天,国家集权主义模式的)严密性的约束,相反,它至少倾向于将破论部分与立论部分(尽管以不完备的方式)联合起来,并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重新引入诸历史模式的方法,在这些模式之间,准确地回归“古代城市”的模式。然而,或者专门召回希腊城邦的“民主”,或者即使我们召回为罗马城市“共和国”,也不能恢复其整个法律体系。
因此,关于国家危机,或者最好说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以及国家形态的危机的结构部分的消极方面,学说状况是这样的,(正如我们马上要考察到的),我们能够/应当谈论相应的“宪法终结”的学说(单数);而不是(在这个学说的分割中的小片段中)“宪法终结”的学说(复数)的多样性;不过,(根据在“序言”中提到的历史—系统的框架),我们能够/应当在唯一的、总的学说中进行构建或者重新组合,该学说也对同一危机的积极方面负责,而且我们因此看到了罗马模式的国家形态(以及立宪主义)的自发性重现。
2、目前关于“宪法不存在”的学说
a. 作为对“宪法不存在”的确证,对英国模式立宪主义的(以及国家形态的)结构危机的消极方面的确证
正如所预料到的,危机的“结构”部分的消极方面实质上至少大部分是理论性的。这涉及到非常有意思的学术思考的路径,并且(尽管近来通过连续性的解决方法,它们获得了弥补),这些思考的路径是远道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能够也应当是与十八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前的讨论关联起来。
不过,在这本小册子中,出于简明的原因,我仅限于且集中于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的最近这些年,在这些年中,我们应当记得一系列有根据且不断增多的批评性思考,它们不仅是由法学家明确提出的,而且也是由政治学家提出的,这些思考以破坏性方式攻击且不断地攻击了这样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当代宪法对公法的实质需要做出了回应,而且它们既已成为十八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前对立的客体:1)对“主体”的确定以及对公共意志形成程序的界定,以及2)从自由权开始,对捍卫权利的手段的确定。事实上,正如我所预料到的,这一系列的批评攻击了这些制度在“英国”的变种:政治的代表以及三权衡平,直到抨击国家—人的概念性假设。这一系列的批评在学术上否定了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的(也就是立宪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概念的存在,它们也否定了(根据我所定义的一种“令人困惑的演绎推理”)我们宪法的存在。
因此,根据这些批评,我们是没有宪法的。
我们没有孟德斯鸠理论化和提出的英国模式的宪法:1)根据宪法和代表体系之间同一性的假设(“我认为在每一部社会的宪法中,如果代表不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虚假的宪法”,对于孟德斯鸠的正统观念,西哀士进行了确认,同时它也被写进了首部法国宪法之中);2)根据宪法与三权衡平之间同一性的假设(“在每一个社会中,权利没有获得保障,权力也没有进行分立,那么就不存在宪法”,对于同样的正统观念,在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得以确认,该宣言不仅被纳入到1792年法国首部宪法之中,而且也被纳入到了1958年的“现行”宪法之中)。
事实上,我们能够且应当说,全球市场及其世界国家的形成现象毕竟仅仅是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的最终阶段,政治代表制度以及三权衡平制度的“蒸发”终究也仅仅是相应的立宪主义的最终阶段。但是,相对于我们现在提出要做的,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话题。
相反,这里,我们现在应当注意到,根据这一系列的批评,如果英国模式的宪法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表现出站不住脚,那么一部罗马模式的宪法如今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重新)出现是可能且可预见的,尽管对其进行解释以及重新提出并不简单。
b. 对如今立宪主义含义的缺乏以及/或者基本概念的模棱两可的确证,即“国家”和“共和国”(以及“民主”和“联邦”)
在立宪主义以及国家形态的结构性危机的诸要素之中,主要的还是对于基本概念含义缺乏的确证,这些概念不仅是这样的立宪主义和国家形态所内生的,而且还是从其它学说和经验中借用来的。
首先,产生了“国家—主权法人”的概念本身,这在宪法起草的时候还是根本的,不过,“神圣的”(尽管是“人工的”和“人类的”)机构可怕却清晰、牢固的概念以绝对排他的方式具有了权力垄断的特点,法学家们,当今对托马斯?霍布斯的追随者们,已经从该概念转变成了与“国家—团体”在一起的“国家—组织—机构”模糊且脆弱的概念(并非必需清晰但却可识别的中介——“市民社会”这种含混的概念,就它而言,翻译但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koinonia politiké概念以及西塞罗的societas civilis概念)。
其次,产生了“共和国”的概念。宪法特别强调了对它的采纳。意大利宪法第139条(第二节“宪法的修改。宪法法律”中两条的第二条)对其修改的可能设置了唯一一条不可触碰的界限:“共和国的形式不能成为宪法修改的对象”。事实上,主流的立宪主义学说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这个概念并不属于它,而且它是在特有语言的背景下使用的,即除了在纲领上含混不清之外,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正在进行的危机突出了这种局限。1968年,《意大利最新学说汇纂》词条“共和国”断言“不可能获得‘共和国’的统一的概念”,“如今,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对立,不仅在法律层面上而且在政治层面上,都显示出微弱的价值”,而且“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如今看来都有点过时了”。
另一个概念继续成为力求在不同背景以及层面上达到的政制秩序话题的中枢,这就是“民主”的概念。然而,在摩西?芬利(Moses Finley)的评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民主》(1971)中,他“发现了”关于词语“共和国”的已经看到的同一现象,该词语表现出在当代缺乏意义。芬利(关于“共和国”得出了与法学家完全相同的结论)写道,对于词语“民主”普遍的赞成对应于对该概念的这样根本的一种轻视,使得任何的分析都变得无用。
关于“联邦”的概念,只需注意到联邦主义学者斯图尔特(W.H. Stewart)统计出来的大约500种不同的词义就足够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即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和国家形态的结构性危机,关于制度的危机,如果它在学说著作的意义上是“学术性的”,那么,关于概念的危机,它就在抨击同样学说的意义上也是“学术性的”。
c. 关于公共意志的形成,政治性代表的“英国”政制制度的不存在的确证
关于政治代表的长久且复杂的批评性思考,其本身并不总是一致的;不过,它总是以及至少抨击了这种制度的本质核心:也就是说,要求是这样的工具,即能够把人(被代表者)的多样性意愿通过其他人(代表)的意愿以统一的意愿表达出来,前者是在没有命令式委托的情况下授权这种功能的。相反,在一般情况下,它并没有对必要的逻辑前提引起注意,由此,被代表者应当预先确立一个更进一步的、新的、“虚构的—人工的”人:“法律的”人,我们称之为“国家”。
二十世纪首要的批评性思考产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政制性”思考。“罗马法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罗马农业史》的作者),在其著名的评论《经济与社会》(初版为1922年)中,确定了两类代表,古代的以及现代的,而且在“最尖锐的对比”中提出了它们,分别称之为“受约束的代表”以及“自由的代表”,后者仅仅是“西方所特有的”,做代表的是被代表人的“主人”(“Herr”)而不是 “仆人”(“Diener”)。1925年,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斥责了“掩盖这样并不微小的改变的企图,即民主的理念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即国家意志并不是由人民形成的,而是由议会这样十分不同的机构形成的,尽管它是由人民选出的。”1931年,卡雷?德?马贝格(Carré de Malberg),写道“一般意志的主权观念已经被用来证实议会本身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的矛盾似乎难以接受任何不服从该话语的人”。事实上,“我们如何能够承认,在我们的公法中,由议会所颁布的决议被作为人民意愿的结果而被公布,而宪法却通常将人民排除出它们的制定?”卡雷?德?马贝格提到了至今仍然有效的1875年法国宪法。不过,同样的批评攻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立宪主义。1975年,关于意大利宪法,康斯坦迪诺?莫塔蒂(Costantino Mortati)坚决认为,在意大利,允许人民实施主权(该宪法第1条庄重地予以确认),无须必要条件的实现,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现行有效的多头政治的制度成为一种议会主权的形式”。
不过,(重新)确证政治代表制度本身不存在(在让?雅克?卢梭之后两百年,并且不管怎样,没有卢梭式的法律意识)的第一位学者不是一位法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 Arendt),在二战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在对现代国家制度批评性思考的背景下,她“发现了”政治代表学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它作为“不可思议之物”而被清除。根据鄂兰的观点,通过现代代表制度,将市民的政治精神“传达”给国家的领导,这种现象是“极度不可思议的”。可能正是因为对政治代表在概念上的清除,汉娜?鄂兰还“发现了”古代城市的政治制度的现实性。不管怎样,很明显的是,这两个“发现”是相关的。
对于政治代表制度本身不存在的重新确证明确且圆满的提出,法学家做出地晚了点。1972年,阿根廷宪法学家乔治?雷纳尔多?瓦诺斯(Jorge Reynaldo Vanossi)将政治代表界定为一种“不可思议之物”。相反,1982年,托雷斯?德尔?莫拉尔(Torres del Moral)认为“禁止命令式委任的理论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从严格的理论性角度来看,该理论在历史上以及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命令式委任]维持了生命,对此,我们完全不用惊奇”。1983年,意大利法学家和议员,费斯凯拉(Fisichella)赞成北美政治学家海因兹?欧拉奥(Heinz Eulau)的主张,根据他的观点(1978年)“如果[...]以某种努力,我们能够大略地指出代表制并非如此,尽管有很多世纪的理论工作,但是我们还是无法说出代表制是什么”。不过,费斯凯拉并没有遵循欧拉奥这样的主张,即该危机涉及“代表的理论而并非代表的制度”,因为他将理论性危机视为制度危机的投影,尽管相对于制度危机来说,理论危机最大的‘速度’能够导致,“当还看不见后者的时候,前者就出现了”。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之间,在意大利,政治代表概念的不存在也成为经典论著的题材:字典式著作。1987年,诺奇拉(Nocilla)和奇奥罗(Ciaurro)在《法学百科全书》中写出了“对于‘政治代表’进行学术性定义的困难”。1991年,在《法学百科全书》中,令费拉里(Ferrari)“感到惊奇的是”(正如托雷斯?德尔?莫拉尔一样)“对于(在传统民主国家观念本身中核心的政治代表概念)进行理论化界定的困难并没有引起公法思想的重要思潮对代表制度危机的抱怨”。
总之:“国王是赤身裸体的!”这所有的让我想到了在法律科学的“不可思议口号”上的思考(另外,它与我的思考并不一致)。
在这种背景下,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这样的创举,即对“命令式委任的禁止”的直接和间接的废除,也就是说对政治代表制度“核心”规则的废除。1999年4月20日,在议会权威的议员中,有足足20名议员向意大利议会提交了“第5923号宪法法律提案[...]关于命令式委任的禁止,对宪法第67条进行修改”,这直接旨在对禁止的废除,在提交的“报告”中,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这种规定现在已经过时了[…]因此,如今,命令式委任的禁止是一种传统的规范”,并且,它处于“与宪法第1条第2款不可化简的对抗之中,根据该款的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这是莫塔蒂〈Mortati〉的观点),而且,与市民的权利一起,通过民主的方法参与决定国家政策(第49条)。99年的宪法法律提案并没有通过,但是,在1993年,通过了一项普通的法律,它规定市长候选人应当将自己的行政计划交由市民投票。事实上,这项义务至今仍然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根据罗马法种类,是一种未完成的法);不过,这些事实却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即通过对其核心规则的废除,对于政治代表制产生了至少倾向性的致命攻击,但是,这样的攻击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既没有学术上的反应,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是一部美国联邦宪法多卷巨著的作者并且在涉及半大陆性质的国家组织(类似于欧盟)中进行了讨论,2000年,他并不局限于对政治代表批评性意见的重复,而且,还通过(在汉娜?鄂兰之后以及沿着她的足迹)在(很明显,尽管仍然是无意识地)回归罗马模式的卢梭式立宪主义的方向上迈出了更进一步,他提出赋予由市民组成的人民以立法权,只留给议会以执行的法定权力。在我所提到的(上述第1段)对盎格鲁萨克逊的—更精确地说—美国的政治学思考的法律—制度层面上,阿克曼的贡献是最成熟的,而且它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废除和抛弃了政治性代表制度并且寻求在古代的“城市”模式中产生出来的人民参与,也就是“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如同现在所说的“慎议民主”)。
d. 对于为了保障权利的三权衡平的“英国”政制制度不存在的确证
因此,根据另一个英国—孟德斯鸠的模式的立宪主义支柱的不存在,实证法学家重新确证了这也是站不住脚的:由三权衡平所提供的对权利的宪法保障。
不过,如同关于政治代表一样,首先提出的也不是法学家,而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仍然在没有考虑让?雅克?卢梭的观点的情况进行了重新提出。1973年,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k von Hayek),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写道:“当孟德斯鸠以及美国宪法之父们在英格兰自发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将一种宪法的理念作为对权力实施限制的总和,他们就创建了一种模式,从此以后,自由主义宪政总是追寻于它。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个人的自由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他们所信赖的手段就是权力的分立。在我们所熟悉的形式中,这种在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行政权之间的划分并没有达到所设想的目的。通过诸宪法手段,无论在哪里,政府都获得了那些思想家们并不想委托给它们的权力。通过宪法形式来保障个人的自由,这第一个企图显然是落空了”。
尔后,法律文本遵循了由冯?哈耶克所重新划定的方向,在这些文本中,最富盛名的当属西尔瓦诺?拉布里奥拉(Silvano Labriola)所草拟的报告,这是在1995年关于宪法改革的(由尼尔德?约蒂〈Nilde Jotti〉主持的)意大利议会两院会议所产生的文件的背景下的。意大利两院会议确认了:“对于现代立宪主义的起源,提出了权力限制的[…]问题:对于这样令人烦恼的要求,与权力分立原则相对立。但是对于该原则进行理论化的随后两个世纪的政治历史,显示出正式的完全衰竭。[…]不想主张的是,权力分立原则本身衰落了[…]不过,残存下来的原则不能适应这样的需要,即相对于该需要,该原则开始被概念化和理论化了,也就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的目的,是通过在主权和经济上有力的社会团体(纳税的选举人)之间权力的分配而实现的[斜体是我写的!]。为此,在当代民主之中,正如意大利共和政体的民主那样,该原则不再起作用(然而,对于在权力行使中保障合法性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它区别于对权力的限制:政治权力是否是合法行使的,是否受限制的,两者是绝对分离且独立的)”。
对于取消由冯?哈耶克以及通过宪法学者拉布里奥拉由宪法改革的意大利两院会议所提出的更不容置辩、更绝对的三权衡平制度意见的设想,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
3、罗马模式的(立宪主义的)国家形态的自发重现与潜在的风险
a. 作为市民参与公共意志形成的“罗马”模式的重现,对城市的“政治”作用在世界范围的确认
关于城市的“政治”经济作用的重现,这种现象是世界范围的。对此,参考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按照惯例以及合理性,(与“全球化”一起)将其界定为“国家危机”现象的积极“方面”。(对此,参见上述段落1.b)
根据上述同样的经济性原因,我不去详细地阐述关于这种特殊现象的专门著作,我仅限于指出对城市政治经济性重现现象的关注也有同样的局限,在关于“国家危机”一般现象的学说中,我已经提到了这样的局限。也就是说:限于该现象的一个部分,这部分肯定是重要的,但在事实上,并非是实质性的(我将其界定为“表面的”),及其对十八世纪法律—政制的重要辩证关系在历史—体系上的关联缺乏认知。
然而,关于城市的政治经济作用重现现象,毫无疑问,更有用的是注意到这个方面,即自治市—联邦的“参与”方式的重现,对于这方面毫无疑问仍然是缺乏研究的,但是就我看来,它无疑是更重要的。在公共意志的形成中,它回归到了对议会制“代表”方式的替代,因此建构了这样的制度性要件,即在此之中,我所界定的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以及国家形态的危机现象的“结构的”部分首要的“积极方面”得以具体化。
关于城市“政治”经济作用重现现象“结构”部分的思考主要是政治学的思考。在五十年代初,鄂兰以及随后的其他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直到今天为止(我提到所谓的“慎议民主”的流派,这是北美宪法学家阿克曼指出的),(如同法学家通常所做的一样)并不限于指出现代政治代表制度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他们正是在古代城市的决议程序中还发现了对于这种无根据性的补救之道。这样的思考对于一种积极的需要和趋势似乎具有指示性,即使从罗马法学者来看,我们从浏览佛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Francesco De Martino)的引文来看,这些重要且有趣的著作似乎是有局限的,恰恰就是由于缺乏卢梭的罗马法解读以及罗马法的卢梭解读,这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至少从法学角度来看,以模棱两可的幼稚方式——人民参与模式:1)仍然在希腊的“城邦—国家”中(尤其是在从克利斯提尼〈公元前507年〉直到被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22年〉的雅典“城邦”中)寻找,而不是在罗马的“国家—自治市”中寻找,而且2)感谢新的信息交流技术所提供的机会,认为如今通过公投制度对其进行重新提出。
然而,这种罗马模式的“自治市—联邦的参与过程”的重现及其对英国模式“议会代表制”方式的倾向性替代,在公共意志的形成中,以在客观上合理且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着,尽管这并没有专门的法学思考的支持和指导。
城市(自治市—共同体),通过议会方式进行运作,在公共决议方面被排除数百年之后,如今带来了这种方式的基础,作为它的本质部分:主权。现今的城市——如同古代城市一样——回归,或者至少想回归到在“市民—主权”中“私人”的转型之中。面对利维坦这种怪物来说,具体的城市以及由市民组成的“具体的”人民成为了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找到了(欧洲城市规划师理事会1998年公布的)《雅典新宪章》非同寻常的转变,在建议中,可以看到“2、一种有意义的参与[…]公共的参与[…]被[…]很多适用常常是高度集中的民主代表体系所僵硬地阻碍了。市民的权利、需要以及愿望的表达以及他们对现象的理解[…]只能通过一种基于在地区以及中央层级上选举出来的代表的体系来达到[…]应当重构计划性组织结构[…]应当严格地适用从属性原则[…]参与的革新形式应当在可能的最小等级中实现,这种地方层级是为了加强[…]市民的主动参与并且鼓励他们参与到市民生活之中。我们需要鼓励社会和文化相近的存在以及表达和集会的空间”等等。
这种“革命”不仅冲击了市镇外部的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制度的关系,还冲击了内部的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制度的关系。事实上,该“革命”不仅针对城市的外部决议的流动(随着在决议方式的方向上的颠倒,这种方式倾向于在共同体中确立自己的根基,这样由后者的决议执行机构所改造,这些决议开始从高的以及最基本的一种意愿[慢慢地]上升为较高层次的概括),而且还针对城市的内部决议机制,对于这些机制,如今由市民重新获得是有意义的。
关于城市的外部方面,我提到两个类似层级的“宪法”草案,分别是欧盟的草案和意大利联邦国家的草案。前者(1991年)是学术性草案,由一位研究阿尔色修斯的专家托马斯?胡戈林(Thomas Hüglin)提出,旨在将欧盟宪法以阿尔色修斯的联邦框架为模式:“社团性的”(也就是“非代表制的”)并且作为一种向上决议的过程来建构,其基础的层级就是城市。后者(1997年)是立法性提案,由关于宪法改革的意大利议会两院会议(由马西姆?德?阿雷玛〈Massimo D’Alema〉主持)提出,旨在修正意大利宪法第二部分现在的标题“共和国的体制”,用一个新的标题“共和国的联邦体制”,并首先替代意大利宪法第二部分第一节目前的标题“议会”,用一个新标题,是这样表示的:“市镇、省、大区、国家”!这样的理念不仅由欧盟表达,尤其是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最近的参见《2007年关于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莱比锡宪章》]),之后还由意大利共和国所表达,尤其是通过宪法第5节的改革(2001)。这两个“宪法性”文本在各自的体制种引入了“从属性原则”(通过该原则可以概括地指出阿尔色修斯的学说),并且它们首先分别在(地区和城市的代表参与的)欧洲“地区委员会”的机构以及意大利“地方自治理事会”的结构中得以表达。“方向的改变”是明显的(纵使还是非常片面且具有可改进性的)。在意大利宪法改革中,第114条(第5节的开始)原来集权制—自上而下的程式:“共和国分为大区、省以及市镇”,这在现今的参与制—自下而上的程式中被颠覆了:“共和国由市镇、省、首府市、大区以及国家组成”。切实地说,欧洲改革者以及意大利改革者似乎都没有考虑到(至少部分地)提出用罗马的政制模式来取代英国的政制模式。缺乏这样的意识就表现在各自改革的偏袒以及随后的局限性上。
关于城市的内部方面,我还要提到1993年第81号法律,规定了“市长、省主席、市镇委员会以及行省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它命令市长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大会提交一份“计划”,基于此,为了管理城市共同体,他向市民要求委任。以这种方式,市民不仅选举了市长,而且还对该市长的“施政方案”做出了决定,这明显与基于命令式委任的宪法性禁止(意大利宪法第67条)的逻辑相对立,因此,如今它置于政治代表制度之外。我提到了一位政治代表的理论家,伊曼纽尔?西哀士,他明确主张,关于这样的制度,在全国政府与“市镇的最小政府”之间并没有区别。另外,还要提到的现象是对拉美关于“参与式预算案”制度的关注和模仿,该制度是在巴西自治市阿雷格里港(一百五十万居民,在南里奥格兰德州)“发明”的,旨在允许市民全部参与市镇预算的形成,考虑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自治、市民管理的改良形式,如今在里奥格兰德州的级别上已经提出了,这就确证了在城市—自治市内外维度之间不可回避的关联。
b. 为了捍卫权利,作为“保民官”方式的重现,保护人制度在世界范围的推广
关于我所界定的英国模式国家形态的危机一般现象的“结构”部分,这第二个积极“方面”就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针对市民进行公共管理的对市民的保护制度(开始于二十世纪,在二战之后):意大利的市民保护人,西班牙的“平民保护人”,法国的“居间人”等等。
关于这种现象,还有大量的法律论著。
然而,这里我不做回顾,主要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参考文献对于法学家来说都是熟知的或者可以轻易知晓的,而且还因为我认为这样的参考文献的价值受到对这种现象解释的限制(被那种参考文献所普遍采纳,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肤浅的,而不是“表面的”),如同北欧视察官制度的推广/模仿一样的,有时被解释为“议会的特派员”。
也就是说,我认为关于北欧视察官在世界范围推广的现象的学说状况,比起城市政治作用在世界范围推广的学说状况来说,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在那个学说中——区别于这个——并没有导致在国家危机的一般现象中对其作为特殊的现象加以察觉。
这种对于“新的视察官”解释的不透明性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它与国家危机现象的关系仅仅局限于这种危机的“结构的”部分,也就是恰恰局限于不被“国家危机”学说“视为”危机的那部分。
相反,倘若市民保护人在世界范围推广的现象被解释为国家危机一般现象的特殊现象,以及在更精确、更正确的意义上,被解释为英国模式的国家形态危机的“结构”部分的两个根本的制度性要件之一的积极方面,那么,它就会获得了另一种意思以及另一种意义。换句话“更简单地”说:有必要理解与三权衡平制度的危机的关联,并通过保民官来对其进行弥补;但是,为了能够这么做,应当利用德?马尔蒂诺所描述的解释模式。
另外,要注意到的是,在前面关于政治性代表制度危机的章节的结论中引用了阿克曼的评论,该评论旨在论述三权衡平制度,对于该制度,阿克曼提出用在人民的“主权的—立法的”权力与狭义上的议会以及政府的“执行—管理”权力之间的二分制进行替代,这要通过一种制度——宪法法院——的介入,根据在拥有主权的人民和拥有执行权的议会/政府之间的中间概念,对此进行深入地重新思考。卡塔拉诺正确地警惕到了在“保民官”概念上与“具有‘宪法修改’功能的机构”的“市民的—自由主义的”概念相重叠,然而,如果阿克曼的建构并不是卢梭的罗马模式,那么我认为,倘若不一致的话,它在客观上至少有接近的趋势。
最后,这种特殊现象与城市“政治”经济作用重现的其他特殊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至少在意大利,只有在自治市范围内,才由市民规定对保护人直接选举的可能,(正如在学说中尖锐观察到的一样)那是真正的宪法性革新。
c. (通过重新对“公法—私法”进行分离)对“国家”概念进行罗马法解读的建议(与“良好的环境”有关)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关于宪政国家的根本制度:公共意志形成的主体和方式以及对自由的捍卫——对权力的限制的方式)在对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以及国家形态)批评的消极现象与罗马模式的国家形态(以及立宪主义的)重现的积极现象之间的中断,并且因此,我们还看到了对这些现象的组织整体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认识的缺乏。
不过,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关于国家的概念)出现了对“国家法人”的概念以及理论上建立在该概念之上的制度的——仍然是孤立但却重要的——批评,这种批评与对先前基于“国家社团”这个概念上的制度(还不能说是“体系”)的重建有机地联系起来。
这种批评以及重构完全地、明确地求助于法律以及罗马法传统。
这种批评和重建从对环境进行有效保护这个问题开始。这种保护可以在“民众诉讼”这个制度中找到。实际上,民众诉讼属于“罗马”法体系并且是市民在程序上参与行使公共权利(它们被理解为这些市民本身的权利)的形式,该诉讼与国家集权主义者的法律逻辑的基本概念(与公私法分离相关的国家—人的概念)以及与政治性代表制度不相容,而且该诉讼与自治市—共同体制度的“政制”作用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历史性—体系性联系(尽管在学术上没有被深入研究过)。
d. “民主”、“共和”以及“联邦主义”这些种类有新的命运,但仍然是不明确的
最后,在确认了“民主”以及“共和”的概念无足轻重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概念的新的关注。这关涉到近来一条学术思考的路径,也就是为人所知晓的“慎议民主”和/或“共和主义”。对于这条路径,有一系列重要的且有根据的词条和著作,它们首先就表示出在“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是一致的,相反在团体和下属的团体中是对立的,它们越来越多地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针对现今的政治体制的批评,在市民参与的形式以及它们在古代城市体制中的保护形式中寻找可替代的解决方法。
我已经提到了那些关于“慎议民主”的作者,这里,我只能重申在那些方面既已做出的观察:1)对政治代表以及三权衡平制度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古代城市民主制度取舍研究的重要性,2)对于希腊政治经验研究的局限,以及不关注罗马法律经验及其中世纪、近代以及当代发展的局限性,这是因为我发现所提出的制度性解决方法在本质上都是“幼稚的”。
对于“共和主义”这个种类的援用应当避免关于“慎议民主”的思考的这种“局限”。事实上,它重新连接了罗马共和的思想及其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发展(对此,创造了一个术语“新罗马的”),以至于重新评价并重新提出了“市镇联邦主义”的实践。然而,正是这种在“共和主义”中所表现出来的思考,在法律层面上似乎是更不可捉摸的:这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而且是在公共意志的形成与法律保障的——对于政制问题来说是基本的——制度上,这就产生了——至少从法学家的视角——对一种不满和一种需求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对这两者的回答。
无论如何,近来关于政治—法律组织形式上的学说争论是有意思的,而且需要考虑到的是,尽管它们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它们还是表现出了我们进行解释的前景。
附录
1、对不存在由经济学所提出的辩证关系的确证(在没有社会的市场与没有市场的社会之间的取舍)以及法律的新要求:罗马法,从对公法的研究出发
根据我们的解释模式,不顾学究式进行“总结(Zusammenfassung)”的努力,这样的重构,即对宪法不存在的空洞理论性的确证,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西方”政制模式的空洞理论性的确证(如果不是作为唯一可以想象到的,也是通过武力来捍卫唯一可能的“民主”),以及在历史和体系上可选择模式的重新出现(大多是自发性的),是存在缺陷的。对于因这本小册子在时间上和篇幅上进行限制而产生的缺漏,我并不担心:这些缺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为了历史的—体系的重构而使用的模式是——就像我相信的一样——正确的话,那么它们肯定是会被填补上的。不过,还有一种至今仍然被我忽略的视角,而我认为有必要——至少——在这个地方提到。这就是经济学的视角。
事实上,在当代的全部进程中,有对经济学作为指导性科学的肯定,这种科学脱离于对法律的伦理性、“上位性”命令,还有对英国模式的立宪主义和国家形态的肯定,在这两种肯定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从肯定了对国家财富基础这样存在瑕疵的理论(所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者”的著作),到肯定了依赖于在劳动组织中专业经济制度的政治代表的法律制度理论(西哀士的著作),再到对马克思理论的肯定,即法律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现在,在立宪主义和主要的国家形态的危机以及经济学的危机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上,当代的经济学也处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更为强烈的表现是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求助)终结了在“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此,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终结”。
不过,历史并没有停步,经济学也应当在理论层面上对其所根据的辩证关系进行一种批评性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要完全遵从同时代的法律现象(对此我们已经简要地阐释过了),而且还要使这些现象更为明朗化。
我认为这种反思有两个倾向。
其中之一涉及企业的组织,也就是本质上具有经济目的的组织,并且存在于这个理论之中,根据该理论,企业劳动者广泛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使得企业行为更有效、更能赢利。不过,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企业组织自上而下严格的等级制、垂直制理论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今天,如果想阅读关于民主的好处的研究,需要查阅的并不是受“激进分子”启发的制度的政治出版物,而是关于企业组织的技术性杂志,它们会谈到从“福特制”向“丰田制”的转变。此外,这个“倾向”产生了欧盟关于对劳动者开放公司管理的“欧洲公司”的指令:这个倾向与同一时期的法律倾向,即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模式的表述(尽管处于危机之中)完全相反,不过,它产生了欧盟推广关于一人公司的制度化的指令。关于对劳动者开放公司管理的指令,我想到了我们宪法的开头“意大利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不过,我首先想到的是在优士丁尼法典中所引用的著名的法律原则“所有的人都同样要承担确定的义务”(C. J., 5.59.5.2)。
然而,另一种倾向关涉的是在促进的经济层面(尽管不是主要的)上政治—地域的组织的效率。关于这种倾向,要提到的是罗伯特?普特南的研究,他不仅通过一系列参数衡量了相对于意大利南部地区来说北部地区更有效率,而且还对此进行了解释。根据普特南的观点,有利于意大利北部的因素是大量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在经济学词典中,“市民”的偏好就是对公共目标“进行投资”。普特南在中世纪市镇制度中找到了根源,事实上,这种经验在欧洲总体上被消灭了,不过,在意大利的南部,一个德国的伟大皇帝,腓特烈二世(他占据了巴勒莫的宫廷并于1224年建立了那波里大学)专门地抹灭了这种经验。大约在普特南的研究15年之后,大家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被腓特烈二世挥霍的“社会资本”是罗马帝国的城市(自治市)系统所积累的。此外,大约150年左右,通过在城市的系统中找到公国的典型要件(在自治市中,“它是我们文明的基础”),西奥多?蒙森将罗马人民界定为一种“所有市民的城市的联盟”;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o Tullio Cicerone)指出,人民是一个为了达到“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并且“构成人民的”是城市,这就是一个社会。我真的找到了有意义的思考,根据这种思考,意大利北部之所以能够繁荣,应归功于(地中海的)“南部”城市—共和国文明的成果,而南部意大利的破败则可以归罪于“北方的”民族王国的文化。
总结:经济学家正在从对“现实”经济辩证关系终结的确证(作为“社会主义”终结的结果)走向对在“市场”和“社会”(或者“社会主义”)之间学理性经济辩证关系“不存在的确证”。如今,经济学家认识到,当代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解释模式(“从理论上来看,现代经济的发展是通过抽掉具有社会性内容的经济关系而达到的”)是虚假的,并且“这样的看法,即在不考虑它们关系的性质的情况下不可能正确地解释经济现象(典型的,比如商品交换和企业行为),总是更为广泛传播的。事实上,经济活动在社会结构中仍然处于根基地位。[...]换句话说,要注意到这样的需要,即要在经济理论领域内消除经济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再换句话说,这种看法可以被视为“一种令人悲痛的失败,经济学研究遭受了阉割,放弃了对在生产和交换领域中作为主角的整个人类,即文明[...]人的研究”。这似乎是明显的,即经济学向法律本位和法律模式的回归正是“罗马式的”,即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的“正义的”法(D. 1.1.1.pr.),这是由卢梭重新提出的:根据上述作者的观点,为了恢复“市民经济”的意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兄弟关系”这个法国革命的概念,时间是“从Montagna的独裁开始”。这里,我还要提到(不知道是否多余)根据盖尤斯的法学阶梯(3.15; 参见Cic. de or. 1.56.273; Fest. 82; Gell. 1.9.12),社会契约根据的是兄弟之间进行协议的基本原理,那种契约是通过合意而产生的。
2、近来重新提出罗马政制模式的试验: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
对于罗马模式的国家形态的重新产生,大多出自其自发的本质(也就是说,缺乏一种适当的学术认知的支持),对此的例外就是1999年12月20日委内瑞拉的拉美宪法,建立了新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取代了先前的“委内瑞拉共和国”。
并不能主张这样的宪法是罗马模式立宪主义令人满意的版本,不管怎样,对此,西蒙?玻利瓦尔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政治上以及学术上有意识地、系统地重新提出那种立宪主义,1999年的委内瑞拉宪法是如今唯一的尝试。该宪法第1条作为基础,提出了共和国的“精神财产”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以及国际和平的价值观”,这是解放者(玻利瓦尔)的“教义”,这种模式,“共和国的罗马”,由共和国的总统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ávez Frías)于1999年8月5日在《全国制宪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
尤其是,这样的宪法坚决地打破了三权制,提出了——与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相一致的——五权。除了立法权(第186条以下)、行政权(第225条以下)以及司法权(第253条以下)之外,还引入了委托给“共和国伦理委员会”(吸收了“申诉专员”、“共和国总检察长”、“共和国总审计长”)的“公民权”(第273条以下)以及委托给“全国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权”(第292条以下)。“公民权”的启示来源于“道德的力量”,由玻利瓦尔于1819年2月15日在安戈斯图拉提交的宪法草案中提出的,“选举权”受到同名的制度所启发,由玻利瓦尔于1826年为玻利维亚起草的宪法草案中提出来的。
该宪法结束了二十世纪并开启了二十一世纪,因此,它定位于罗马模式的立宪主义以及国家形态:这是在这样明显的过渡背景下,即在拉丁美洲,从古巴“社会主义”共和国前总统(宪法第1条)交接给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新总统。